北方的旅游景點(diǎn),北方的旅游景點(diǎn)推薦
北方的旅游景點(diǎn),總是能夠讓人心馳神往,在這片廣袤而神秘的土地上,藏著無數(shù)讓人流連忘返的美景。每到一處,都是一段別樣的旅程,帶給人們別樣的感受與啟發(fā)。正如李白所言:“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fēng)流人物。”……
2024-0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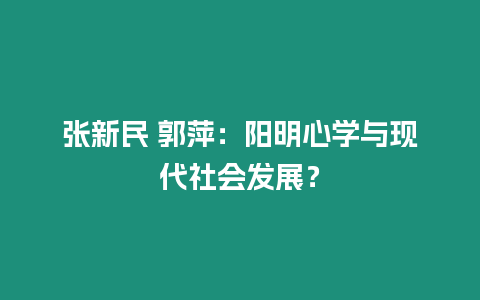
原載《國(guó)際儒學(xué)論叢》總第5期,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8年6月
編者按:近年來,陽明心學(xué)成為儒學(xué)研究中的一個(gè)熱點(diǎn),但陽明心學(xué)對(duì)于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發(fā)展具有怎樣的意義和啟示還需進(jìn)一步闡明,事實(shí)上唯有深入理解這個(gè)問題才能從積極的意義上發(fā)展陽明心學(xué)。為此,編者約訪了貴州大學(xué)中國(guó)文化書院榮譽(yù)院長(zhǎng)張新民教授,請(qǐng)他就陽明心學(xué)與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的相關(guān)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本文為此次訪談的實(shí)錄。
郭萍:近些年,關(guān)于陽明心學(xué)的研究非常熱,而您在這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成果。我首先想請(qǐng)教的是從一個(gè)宏大的歷史發(fā)展來看,您認(rèn)為陽明心學(xué)在儒學(xué)的歷史上起到了一個(gè)什么樣的作用,對(duì)我們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發(fā)展有什么價(jià)值?陽明心學(xué)引導(dǎo)著一個(gè)什么樣的價(jià)值取向?我想聽聽您的看法,因?yàn)楝F(xiàn)在對(duì)這個(gè)問題有一些不同的觀點(diǎn)。
張新民:這個(gè)問題很大。
郭萍:是很大,但也是一個(gè)前提性的問題,否則會(huì)陷入盲目研究,還會(huì)平添亂象。早前李澤厚就已經(jīng)指出陽明心學(xué)開啟了一種現(xiàn)代性的可能,也有學(xué)者把陽明比作中國(guó)的托馬斯·阿奎那,或者比作中國(guó)的馬丁·路德。您怎么看待陽明心學(xué)在中國(guó)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角色?
張新民:就大問大答罷。陽明心學(xué)是一套學(xué)問體系,可以稱為心的哲學(xué)。它主要是講精神,也可稱為精神哲學(xué),但與西方哲學(xué)不同的是,必須有一套工夫系統(tǒng)來加以配合,實(shí)踐性的維度十分突出,是實(shí)踐性的心靈哲學(xué)或精神哲學(xué)。
我們今天講,人的存在可以分為很多層次:物質(zhì)生命、文化生命、政治生命、藝術(shù)生命、宗教信仰生命等等。但是無論怎樣劃分,也不管東方西方,人類在物質(zhì)性的生命之上必然有一個(gè)精神性的生命,超越性的生命。這個(gè)生命當(dāng)然不能脫離我們的肉體,它一定要寄放在身體之中,但是僅僅用身體來講人的存在,沒有精神或至善的德性,那人不是變成行尸走肉了?反過來,假設(shè)沒有一個(gè)身體的存在,沒有身體來安頓、寄放這個(gè)精神或至善的德性,那不就成了一個(gè)空中的漂浮物,一個(gè)空中的精靈,變成虛無縹渺的神仙了?所以在這個(gè)意義上,人是一個(gè)精神與身體的統(tǒng)一體,就是他的肉體生命和精神生命是打成一片的,是身心一元的存在。有趣的是,無論身或心,中國(guó)人都從不輕易否定,而是要通過身心一體的修養(yǎng)方式,實(shí)現(xiàn)人的在世(不是離世)的超越。
我們這個(gè)物質(zhì)性的生命,生理的、心理的生命,當(dāng)然要做好安頓,不能不發(fā)展好,但人的發(fā)展絕對(duì)不僅于此,他一定還有自己的內(nèi)在心靈世界,有不能化約為物質(zhì)的精神要作安頓和發(fā)展,而且一定是更高一層的超越性的安頓和發(fā)展。就是我們把我們生理的生命、心理的生命,亦即馬克思講的衣食住行的經(jīng)濟(jì)物質(zhì)生活安頓好以后,我們還有一個(gè)精神性的更高層次的發(fā)展。精神性的發(fā)展相對(duì)來講其實(shí)更重要,因?yàn)闆]有一個(gè)精神性的發(fā)展,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很多危機(jī)——道德淪喪、價(jià)值迷失、信仰坍塌——統(tǒng)統(tǒng)都跟這個(gè)問題的存在有關(guān)。所以,物質(zhì)與精神的發(fā)展,應(yīng)該像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一樣,是需要共同配合并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我們不能用一個(gè)方面來否定另一個(gè)方面,但在某種情況下,尤其對(duì)中國(guó)士大夫或文化精英而言,我們?cè)谥v利和義的時(shí)候,是不是更要突出義呢?甚至失敗后關(guān)到牢里,像文天祥一類的仁人志士,他寧可舍棄一切世俗富貴也要為他的精神生命做一個(gè)超越性的選擇。這就是殺身成仁,以一己生命之犧牲來成就更高的價(jià)值,彰顯出人性的莊嚴(yán)和道德的偉大,開顯出宗教性的超越世界。但宗教式的道德只能出自知識(shí)精英的自覺或自律,卻不能以外爍的方式強(qiáng)加于一般民眾或普通百姓。
回頭來看陽明,他是講心的——心是他的哲學(xué)思想的中心范疇——心一定有能知的功能,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人的認(rèn)知能力,是人認(rèn)識(shí)客觀世界各種事物天生就有的內(nèi)在理性分析能力。客觀世界的事物是紛紜復(fù)雜的,藍(lán)天、白云、高山、大海……都既可以是我們觀賞的景物,也可以是我們認(rèn)知的對(duì)象。因此,能知(心)必然是一,所知(客觀事物)必然是多;我們只能以一來統(tǒng)攝多,而不能以多來撓亂一。同樣地,以形上人性為依據(jù)的道德心是一,以他者關(guān)系為對(duì)象的道德行為則為多,一可以指揮多,多則聽命于一。也就是說,面對(duì)不同的道德行為對(duì)象,主宰的心都可以發(fā)出絕對(duì)律命:見父知孝,見兄知悌,見朋友知信,見國(guó)家知忠,表現(xiàn)為不同的道德行為,形成多種多樣的道德節(jié)目,但如果追溯其行為的本源,都無不植根人的道德本心。可見心的能知一旦展開或起用就必然涉及一定的對(duì)象(所知),不能不是一種意向性的活動(dòng),而多種多樣的事物的敞亮和開顯也有賴于心的展開或起用,當(dāng)然就可將其定義為心所統(tǒng)攝的對(duì)象性所知了。所以,人通過后天的培養(yǎng)不斷提高了心的認(rèn)知能力,也就意味著不斷提高了它的統(tǒng)攝活動(dòng)方法,不僅能夠更好地以一馭多,把握紛紜復(fù)雜的現(xiàn)象世界,而且能深入心源判斷或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建構(gòu)起一個(gè)真正屬于人的主體世界。
正是從這一意義脈絡(luò)上講,心既是人的靈性生命的象征,也是人的自我主體性的隱喻,顯示人永遠(yuǎn)有一個(gè)能跟世界打交道的神感神應(yīng)的奇妙精神世界。離開了心,人就難以奢談自覺或自律,更遑論什么認(rèn)知或?qū)嵺`?作為一個(gè)道德主體,正是由于心的自覺或自律作用的存在,人才擁有了自由意識(shí),可以發(fā)出相應(yīng)的道德律令,能夠派生出各種各樣的倫理行為。倫理行為必然指涉一定的對(duì)象,當(dāng)然就離不開實(shí)踐化和社會(huì)化的人生發(fā)展維度,而人也必須對(duì)自己的行為可能產(chǎn)生的后果負(fù)責(zé)。實(shí)踐化和社會(huì)化的過程必然涉及各種復(fù)雜的群己關(guān)系,我們當(dāng)然就應(yīng)該建構(gòu)倫理學(xué)或道德實(shí)踐學(xué)一類的理論體系。但也有必要反觀心源,不僅要在作用層上審視白己的心理活動(dòng),更要契入本體層直觀寂然不動(dòng)的心性形上世界。這就必須了解本心何以能夠與人性相通,或者說能凝聚理性和情感的心的后面還有一個(gè)廣袤的可以“性”來表征的形上世界,形成現(xiàn)代人不可或缺而又有傳統(tǒng)資源支撐的新心性學(xué)或新心性實(shí)踐學(xué)。
我們現(xiàn)在看,傳統(tǒng)心性學(xué)講“心”必然涉及形而上的“性”,一說到“性”又不能不與更加超越的“天”相通,可說是即“心”即“性”即“天”三位一體了。從“心”的形上層面看,“心”之體顯然是寂然不動(dòng)的;但從心的形下層面看,“心”之用必然又是感而遂通的。“心”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不僅形上與形下打成一片,而且存在與活動(dòng)也不可二分。當(dāng)然,儒家講心只是渾全地講,佛教講心則十分細(xì)密。佛教的心可細(xì)分為五十二心所,心的后面有末那識(shí),未那識(shí)又連著阿賴耶識(shí)。但早在禪宗講明心見性之前,儒家就講存心養(yǎng)性了。而儒家既講存心養(yǎng)性,當(dāng)然就意味著心性一體,心與性一樣都是可以超越的,能夠與形而上的天道貫通的。《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與“天”難道不是相通的嗎?因此,倫理學(xué)或道德實(shí)踐學(xué)如果不能違悖人性的話,就必須有一個(gè)形而上的哲理奠基。這就是為什么中國(guó)的道德哲學(xué)從來都難以脫離心性學(xué),我們只能將其歸屬于較諸普通倫理學(xué)更為深刻的道德形上學(xué),即使晚出的王陽明的良知說也不能例外,他是孔孟之后深化傳統(tǒng)道德形上學(xué)的第一人。
以“心”來表征人的靈性生命或精神價(jià)值,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記它的超越性的向度。從整體上看,中國(guó)人也是透過自己的心靈來發(fā)現(xiàn)本體世界的存在,實(shí)現(xiàn)自己即出世即入世的精神超越的。這是一種內(nèi)外打通的超越方法,較之其他各種異國(guó)宗教,一樣能莊嚴(yán)人生,莊嚴(yán)社會(huì)。心的活動(dòng)的另一個(gè)重要向度,就是生活世界的道德實(shí)踐,必須轉(zhuǎn)化為真實(shí)的倫理行為,同時(shí)也重視知性活動(dòng)及其實(shí)踐,因而必然是可以顯現(xiàn)的和能夠經(jīng)驗(yàn)的。可見中國(guó)文化所講的“心”涵蓋包圍十分廣大,王陽明甚至認(rèn)為當(dāng)與太虛同體。這不僅極大地凸顯了“心”自身的開放性和靈動(dòng)性,而且也示明了“心”與宇宙的同構(gòu)性與同源性。
王陽明之前的孟子,他也講到良知良能,良知不慮而能,不學(xué)而知。陽明的“致良知”則是把孟子所說的“良知”與《大學(xué)》“格物致知”之“致知”整合為一體,給予了創(chuàng)造的解讀和發(fā)揮,形成了與程朱理學(xué)有別的另一套心學(xué)系統(tǒng),充分地肯定了人的存在及其道德實(shí)踐的價(jià)值與意義,認(rèn)為它具有某些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的特征,我以為并非就是牽強(qiáng)附會(huì)的個(gè)人觀察的結(jié)論。
郭萍:如果把您講的這段話簡(jiǎn)單地做一個(gè)總結(jié),就是您認(rèn)為陽明是以心來安頓現(xiàn)代人的精神和信仰,起到了一種觀念上的導(dǎo)向作用。另外,您認(rèn)為,陽明所高揚(yáng)的那種人的主體性觀念,是一個(gè)群體的主體性,還是一個(gè)個(gè)體的主體性?因?yàn)殛柮魇菍?duì)朱子理學(xué)的翻轉(zhuǎn),他以自己的心、個(gè)體的心去回應(yīng)這樣一個(gè)天理的東西,所以有人把陽明類比于馬丁·路德,而我們知道,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其實(shí)是強(qiáng)調(diào)個(gè)體跟上帝溝通的自主性,凸顯了個(gè)體的主體價(jià)值。那么,陽明是不是也具有某種個(gè)體主體性的導(dǎo)向?
張新民:是的。把陽明同馬丁·路德相比較,我認(rèn)為是有可比性的,因?yàn)闊o論馬丁·路德或王陽明,他們都認(rèn)為人的俗世存在應(yīng)該有一成德的發(fā)展方向,只是一個(gè)認(rèn)為成德的動(dòng)力來自高高在上的上帝及其無聲的召喚,自己的一切行為都應(yīng)該對(duì)救贖的上帝負(fù)責(zé),是自上而下地實(shí)現(xiàn)人的主體自由,難免不有外在他律的特征;一個(gè)認(rèn)為成德的動(dòng)力來自人人均有的良知及其流行發(fā)用,自己的一切行為都應(yīng)對(duì)能夠自作主宰的良知負(fù)責(zé),是自內(nèi)而外地實(shí)現(xiàn)人的主體自由,更多地具有內(nèi)在自律的特點(diǎn)。二者的人生修養(yǎng)與思想境界也有一定的差距,王陽明顯然遠(yuǎn)比馬丁·路德含蓄高雅得多。然而十分有趣的是,作為同一時(shí)代、不同地域的兩位重要?dú)v史人物,他們都因?yàn)樽陨硭枷雽W(xué)說的快速傳播,引起了兩種形態(tài)差異很大的文化自身內(nèi)部的爭(zhēng)議,從而分別導(dǎo)致了中國(guó)和歐洲兩大思想文化體系的重大變化和調(diào)整。
我們看馬丁·路德進(jìn)行宗教改革以后,事實(shí)上就意味著不必通過特定的天主教的教會(huì)或神父,人人都可以憑借信心直接與上帝溝通。這不僅削弱了教皇的宗教權(quán)威,而且也肯定了人的世俗成就。王陽明的良知無人不具,成圣成賢的可能決非皇權(quán)所能壟斷,判斷是非的標(biāo)準(zhǔn)只能訴諸人的內(nèi)在良知而非訴諸任何外部權(quán)威。這也直接肯定了人的世俗存在的價(jià)值與意義,暗中削弱了帝國(guó)政治對(duì)是非判斷的壟斷權(quán)。他們兩人一西一東,先后不約而同地發(fā)聲,針對(duì)不同的政治生態(tài)文化,都有振聾發(fā)聵的重大歷史意義。
大家知道,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產(chǎn)生的一個(gè)非常重要的原因,至少資本主義的興起都發(fā)生在新教徒勤勉工作的地方。新教徒的一套宗教信仰系統(tǒng)和倫理體系,恰好為資本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支持。他們普遍認(rèn)為必須通過自己勤勞致富所獲得的世俗成就,才能證明自己可以拿到上帝垂愛所發(fā)出的選票,進(jìn)入代表超越界的天堂,超越界與出俗界雖是不可通約的兩個(gè)世界,但人卻可以憑借信仰和勤勉來決定自己的終極選擇。王陽明生活的時(shí)代也是商人階層頗為活躍的時(shí)代,良知存在的普遍性顯然不可能將商人排斥在外,因而以正當(dāng)合理的手段發(fā)財(cái)致富一樣是符合天道性理的行為,他的“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為圣為賢”一類的說法,恰好也為商人邁入“圣域”打開了大門,至于良知說更為世俗社會(huì)的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提供了必要的倫理支持。當(dāng)然,與馬丁·路德認(rèn)為一切善功都來源于對(duì)外在的基督的信靠和上帝的義不同,王陽明則認(rèn)為道德實(shí)踐的可能性即來源于人人無欠無缺的內(nèi)在天賦良知,
超越界與世俗界在他那里依然是不可分的,因而個(gè)人的德性修養(yǎng)遠(yuǎn)較世俗成就更顯得重要。
從根本上講,良知人人都有,即使圣人與愚夫愚婦也無任何區(qū)別。因此,如同基督教所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樣,良知面前也人人平等。這種人人均有的良知當(dāng)然是個(gè)體性的,如同證悟良知本體是當(dāng)下每一個(gè)人反身內(nèi)照即可以做到的事一樣,每一個(gè)人的良知判斷和決策也決非任何他人所能替代。只有面對(duì)自己的良知無悔無愧,才能最大化地彰顯道德主體的最高自由。尤其是個(gè)人必有的良知與涵蓋一切的天道本來一體不二,我們當(dāng)然也可說良知是普遍性的天道的個(gè)體性落實(shí),同時(shí)也可用推己及人的方法,將這一特殊性擴(kuò)廓為人人如此的普遍性,形成特殊與普遍辯證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因此,從本體與工夫一本不二的關(guān)系出發(fā),則可說普遍性是根據(jù)形上超越的本體世界來講的,個(gè)體性則是針對(duì)形下實(shí)踐的經(jīng)驗(yàn)世界而言的,只是形上超越的世界與經(jīng)驗(yàn)實(shí)踐的世界依然是一個(gè)世界。如果比較馬丁·路德改革后的西方新教,則可說它的世俗化發(fā)展傾向盡管越來越明顯,但超越界與世俗界仍然隔而不通,上帝之城與俗世之城只能是兩個(gè)世界,則可說陽明的良知乃是即存在即活動(dòng)的,它實(shí)際已決定了超越界與世俗界顯然是可以打通的,兩人的不同所凸顯的正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在馬丁·路德那里,人的義的實(shí)現(xiàn)一定是上帝的救贖使命的實(shí)現(xiàn);而在王陽明這里,人的道德的實(shí)現(xiàn)則只能是良知本體流行發(fā)用的實(shí)現(xiàn)。
良知作為人的存在的本體之知,既是“心”的昭明靈覺,又是“性”的開顯發(fā)竅,因而既是超越的,又是可以經(jīng)驗(yàn)的。超越即表征了與形而上的“性”的相通,經(jīng)驗(yàn)則意味著能夠落實(shí)為人的實(shí)踐性生活。良知與本心依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guān)系。因此,原初本源的良知,一定具有“知”的功能,能夠轉(zhuǎn)化為多種多樣的社會(huì)化的倫理行為,與“心”相較則更加突出了道德的維度。例如,禪宗也講心,儒家也講心,禪宗跟儒家的區(qū)別究竟何在呢?王陽明的與本心本性一體不二的良知說,顯然更加突出了人的道德主體性,有著明顯的道德實(shí)踐的價(jià)值訴求,較之禪宗多講“靈知”而決少講“良知”,亦不關(guān)心俗世社會(huì)人倫秩序的建構(gòu)活動(dòng),二者之間依然有著清晰的邊界區(qū)分或取向差別。
進(jìn)一步分析,佛教盡管不壞世間法,但更關(guān)心的是出世解脫,未必就完全肯定現(xiàn)實(shí)世界,更不可能承擔(dān)治國(guó)平天下的倫理責(zé)任。王陽明的良知說之所以傳承了孔孟正脈,即在于他是形上與形下兩重世界一齊通透,既關(guān)注形下世界人間合理秩序的合理建構(gòu)活動(dòng),又重視直入形上世界以獲取融然一體的本體論奠基。他的良知說內(nèi)(主)外(客)徹底打通,不僅心之理與天地萬物之理一體不二,甚至心靈秩序和人間社會(huì)秩序也相呼相應(yīng),可說徹底消解了馬丁·路德成德工夫缺少心中之理的支撐的困難,當(dāng)然顯得更加圓融和究竟。在馬丁·路德那里,只能將至善歸于上帝,超越的終極根據(jù)亦在天國(guó)而不在人世;在王陽明這里,至善即是心之體,超越的根據(jù)即為徹上徹下的人性良知而不再將其高懸于天上。故黃宗羲說自王陽明“指點(diǎn)出良知,人人現(xiàn)在,一返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gè)作圣之路,故無姚江(陽明),則古來之學(xué)脈絕矣”,當(dāng)是深得陽明學(xué)說三昧之言。可見良知說的根本關(guān)懷仍為每一個(gè)生命個(gè)體價(jià)值與意義的實(shí)現(xiàn),目的訴求依然是儒家一貫強(qiáng)調(diào)的圣賢人格形態(tài)的最終達(dá)致。
成圣賢的本體依據(jù)在哪里?如果要成圣成賢,一定應(yīng)該有一個(gè)本源的終極性的根據(jù),王陽明經(jīng)過長(zhǎng)期的心路跋涉歷程,才找到了他自己始終都堅(jiān)信不疑的答案:“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從龍場(chǎng)悟道揭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再到晚年總結(jié)為“致良知”,他也經(jīng)歷了一個(gè)很長(zhǎng)的生命磨煉過程,前前后后不知有多少驚濤駭浪迎面襲來,不僅透過自己的實(shí)踐活動(dòng)高揚(yáng)了人的主體性,而且也說明生命成長(zhǎng)乃是一個(gè)不斷提升的過程。只有以開放的勇氣不斷地反省自己和提升自己,才能一步一步地契入真理性的存在境域。
有必要注意的是,王陽明所說的良知,作為一種德性之知,當(dāng)然是與天道相通相貫的。因此,從這一理論脈絡(luò)看,盡心即可以知性,知性則一定知天。道德實(shí)踐的過程就是不斷超越的過程,超越的過程即盡心知性知天的過程。所以,如果追問主體的價(jià)值根源,則可說既來自內(nèi)在的能夠依本起用的良知,必然可顯現(xiàn)于道德界,也來自外在的可以生物成物的天德天道,必然遍布于存在界,而決不與權(quán)力世界有任何直接的來源性關(guān)涉。王學(xué)陣營(yíng)中盡管有狂狷精神的人很多,不能說與良知說高揚(yáng)了人的主體性毫無關(guān)系,但也可見他們所抱持的處世倫理未必就與帝國(guó)倫理一致,不僅與代表官學(xué)系統(tǒng)的程朱理學(xué)有很大區(qū)別,而且也折射出張揚(yáng)個(gè)性的時(shí)代精神。
我們前面已經(jīng)一再?gòu)?qiáng)調(diào),良知實(shí)踐是天道的個(gè)體化落實(shí),但也有可能引發(fā)出另一個(gè)問題,即有沒有可能產(chǎn)生集體或公共良知?社會(huì)需不需要集體或公共良知?如果良知實(shí)踐完全是個(gè)體化的,人與人之間又當(dāng)如何通約?我想無論朱熹“講性即理”,或者陽明講“心即理”,他們都是要將人的存在之理與天的存在之理打通的。天的存在之理當(dāng)然就是天道或天理,天道或天理必然是客觀的。天道或天理就是萬物生生不息之道和生生不息之理,它必然是和人的生生不息之道和生生不息之理相通的。主體不但不會(huì)與世界割裂,甚至本來就是一體的,否則便談不上仁者以萬物為一體,更遑論良知是“萬化”的本體論根源。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陸象山所說“千萬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因此,我們當(dāng)然可以依據(jù)天道人心共同存在之理來建構(gòu)集體或公共良知。譬如從消極方面講,對(duì)權(quán)力的批判,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譴責(zé),對(duì)壓迫的反抗,歷史上一個(gè)民族的聲音可謂不絕于耳;從積極方面看,對(duì)人性美德的歌頌,對(duì)正義力量的贊揚(yáng),對(duì)人間不幸的同情,歷史上一個(gè)民族的聲音也從未間斷。這些都足以證明人類集體或公共良知的存在,當(dāng)然都可以重新激活為現(xiàn)代性語境下的客觀現(xiàn)實(shí),轉(zhuǎn)化為人間社會(huì)當(dāng)下的正義行為,從而參與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秩序建構(gòu),改變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現(xiàn)象——包括制度架構(gòu)安排上的不斷損益與完善——開辟出新的充滿人文價(jià)值理想的文化發(fā)展方向。
人是要生存生活和創(chuàng)造發(fā)展的,創(chuàng)造發(fā)展不僅符合天道的活潑化育生機(jī),而且也契應(yīng)良知的生息不已之理,因而我們既要靜觀默會(huì)客觀的天道,也要反觀體證主觀的良知,二者合為一體,既是天心又不離人心,體現(xiàn)了形上與形下的兩個(gè)評(píng)判向度,都是政治合法性必具的基礎(chǔ)。儒家的理想不僅是人與其打交道的世界必須合理,更重要的是要以人的道德人文精神來化成天下,形上與形下兩個(gè)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是不可或缺的,同時(shí)也必須立足于民族集體的歷史經(jīng)驗(yàn)之上。
今天我們?nèi)绾沃v陽明的學(xué)問,如果容許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或發(fā)揮,集體或公共良知及與之相應(yīng)的制度化建設(shè),就不能不作為重要的思考范疇納入其中。但提倡集體或公共良知并非就意味著消解個(gè)體良知,缺少了個(gè)體良知的真實(shí)到場(chǎng)談不上集體或公共良知,二者之間應(yīng)是相互激勵(lì)和相互助長(zhǎng)的關(guān)系。
以人人認(rèn)同的普遍良知共識(shí)為基礎(chǔ),當(dāng)然可以建構(gòu)能見之于社會(huì)生活實(shí)際的公共道德,協(xié)調(diào)人與人之間的禮義交往,形成相應(yīng)的社會(huì)公共空間秩序。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以人為本的社會(huì)秩序建構(gòu)工作,我認(rèn)為必須引起社會(huì)公眾的認(rèn)真思考。無形的良知之道或良知之理開顯出來的公共秩序空間,當(dāng)然可以轉(zhuǎn)化為人人都參與其中的有形社會(huì)生活,不僅足以感受到人性或良知相互傳遞的溫暖,而且更能催生出活潑潑的創(chuàng)造生機(jī)。
由此可見,如果要真正理解關(guān)乎我們存在方式的良知學(xué)說,尤其是將其轉(zhuǎn)化為自己的行為方式或生活內(nèi)容時(shí),一方面我們當(dāng)然不能排斥個(gè)體性或個(gè)體自由,因?yàn)榱贾鳛閷?shí)存主體本來具有的生命境界,必然是要?dú)w到自由的,不自由的良知還能叫良知嗎?我們能把良知捆綁或束縛起來嗎?良知的不學(xué)而能、不慮而知已決定了它是自由的。王陽明的臨終遺言“此心光明,亦復(fù)何言” ,也說明了他晚年生命境界的自在或自由。另方面我們也有必要建構(gòu)公共良知或社會(huì)良和,不能將集體良知或公共良知排斥于良知學(xué)說之外。例如,康德講的“位我上者燦爛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一場(chǎng)森林大火漫延開來了,大家都按良知發(fā)出的道德律令趕快去救,每個(gè)人的行為都是源自良知的自發(fā)性個(gè)體行為,但救火的不是一個(gè)人而是很多人,個(gè)體良知的當(dāng)下呈現(xiàn)已轉(zhuǎn)化為集體良知的當(dāng)下呈現(xiàn),個(gè)體道德行為也轉(zhuǎn)化為集體道德行為,場(chǎng)面顯得十分英勇,令人油然生起敬意。這當(dāng)然就是集體或公共良知存在的生動(dòng)事例。現(xiàn)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將這種集體性的良知進(jìn)一步公共化或客觀化,如防火公約及相關(guān)措施的制訂,救火英烈的表彰及其儀式活動(dòng)的制度化安排等等,按照儒家仁內(nèi)禮外的制度化設(shè)計(jì)原則,都不過是公共良知本體由內(nèi)而外展開實(shí)現(xiàn)必有的現(xiàn)象而已。再進(jìn)一步專業(yè)化或制度化,則可納入政府管理的范疇,即設(shè)立公共專業(yè)消防機(jī)構(gòu),以救人救物減少犧牲或損失為第一工作原則,當(dāng)然即可看成是公共良知的進(jìn)一步制度化。其它如辦醫(yī)院,辦學(xué)校,辦慈善院,辦警察機(jī)構(gòu)等等,盡管都?xì)w屬于政府職能管理部門,但仍應(yīng)是社會(huì)公共良知客觀化的結(jié)果。而政府管理部門既然必須率先成為社會(huì)公共良知的表率,人民就有權(quán)按照社會(huì)公共良知的標(biāo)準(zhǔn)對(duì)其進(jìn)行監(jiān)督和批判,只有不斷推動(dòng)政府與民眾之間積極正面的良性互動(dòng),才能更好地形成合理健康的社會(huì)公共禮義秩序。政府官員的秉公辦事原則及公正服務(wù)立場(chǎng),既是社會(huì)公共良知的制度化反映,也是個(gè)人良知的個(gè)體化到場(chǎng),正是透過集體良知與個(gè)人良知的良性交叉互動(dòng),我們才能更好地建構(gòu)高效優(yōu)質(zhì)的現(xiàn)代公共秩序。如果背離了天道,背離了人性,背離了良知,背離了道德,無論古今中外,一切公共制度秩序都會(huì)因合法性的喪失而潰敗解體。
社會(huì)制度的建構(gòu)既然不能不有良知的到場(chǎng)或參與,所謂到場(chǎng)或參與又必須具有廣泛性或普遍性,即不僅要聽到地方鄉(xiāng)村聚落的良知輿論,如古代的民間采風(fēng),而且也要聽到荒郊野外寂寞個(gè)體的孤獨(dú)發(fā)聲, 如古代的舉逸民,然后又據(jù)此隨時(shí)調(diào)整政策或損益制度,最終則形成一套歷代先賢向往的禮樂典章制度。因此,這就很難設(shè)想牟宗三先生所講的“良知坎陷”會(huì)產(chǎn)生什么后果。“良知坎陷”只能是價(jià)值理性的自我犧牲,人的存在的徹底異化,私欲烈火的熊熊燃燒,邪惡魔鬼的洋洋得意。好人的無能為力恰好是邪惡滋長(zhǎng)的原因。所以,與“良知坎陷”的說法相反,我們應(yīng)多講“良知的挺立”。王陽明的良知學(xué)說,今天看來仍不會(huì)過時(shí)。
良知的一大特點(diǎn)就是能夠知是知非,我們前面說判斷是非的標(biāo)淮不在皇權(quán)而在人人都有的良知,亦即判斷是非的標(biāo)淮不在權(quán)位高低而在與天道相通的良知,因而每一個(gè)體都可以依據(jù)良知批判專制皇權(quán),批判一切違背人性的腐敗現(xiàn)象,良知本身就是批判精神的一個(gè)發(fā)動(dòng)源泉,救世使命的一個(gè)召喚圣地,既源源不斷主動(dòng)提供價(jià)值,又聲聲呼喚自覺前行上陣,無怪乎王陽明“龍場(chǎng)悟道”之后,首先傳播的就是“知行合一”學(xué)說。一切真正的道德行為都來自良知主動(dòng)發(fā)出的森嚴(yán)律令,道德行為的背后都有一個(gè)良知自做主腦的動(dòng)機(jī)世界,我們服從的只是這個(gè)動(dòng)機(jī)世界而非任何外部世界大大小小的權(quán)威,只有服從良知發(fā)出的道德律令才可能具有自由精神和真實(shí)的倫理行為。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陽明才認(rèn)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強(qiáng)調(diào)一念發(fā)動(dòng)就是行了。他所說的其實(shí)正是內(nèi)在隱蔽的良知之“知”與外在顯現(xiàn)的良知之“行”的統(tǒng)一。我們不能將良知之“知”從良知之“行”中剝離出來,無論隱蔽的源頭的動(dòng)機(jī)世界或顯現(xiàn)的行為的效果世界,都是人類戰(zhàn)戰(zhàn)兢兢審慎修行的具體場(chǎng)域。
這固然是對(duì)人類主體性充滿熱情的高揚(yáng),但也可看成是憂心忡忡的哲人勸勉或告誡。
我們既然承認(rèn)有集體性的良知,當(dāng)然就應(yīng)該有集體性的道德行為,即使是個(gè)人性的道德行為,也不能不受到社會(huì)公眾輿論的監(jiān)督或檢驗(yàn),如果真能做到表(外在行為世界)里(內(nèi)在動(dòng)機(jī)世界)如一,我想總是會(huì)為社會(huì)公共良知認(rèn)同或接受的。這正是我們重建社會(huì)禮義文明秩序的人性基礎(chǔ)。但必須警惕或注意的是,與個(gè)體性的良知一樣,人類良知有時(shí)也會(huì)集體性地泯滅,如上個(gè)世紀(jì)納粹極權(quán)主義的興起,更早的西方殖民主義擴(kuò)張,黑暗時(shí)代的騙人宣傳桎梏了大多數(shù)人的心靈,良知的光亮反而只能在少數(shù)個(gè)別人身上發(fā)現(xiàn)。歷史上的真理傳播者,往往都是少數(shù)特立獨(dú)行的人。我們回頭看王陽明身處其中的明代歷史,如同受到教皇教諭定罪的馬丁·路德是一個(gè)人面對(duì)權(quán)力世界一樣,受到廷杖之辱的王陽明也是一個(gè)人面對(duì)權(quán)力世界,但究竟是權(quán)力的掌握者擁有良知的勇氣,還是孤單敢言的王陽明擁有良知的勇氣?我想歷史決不會(huì)因?yàn)闄?quán)力世界暫時(shí)表現(xiàn)為多數(shù)就站在他們一邊。所以,我們決不能講集體性就排斥個(gè)體性,講個(gè)體性就排斥集體性,我們只能站在良知和真理的一邊說話。歷史的吊詭是個(gè)體性可能包含著集體性,集體性可能包含著個(gè)體性,肆意地夸大集體性而否定個(gè)體性,或者一味地強(qiáng)調(diào)個(gè)體性而貶低集體性,都有失中國(guó)文化一貫強(qiáng)調(diào)的“允執(zhí)厥中”的中道精神。
嚴(yán)格地說,集體性就是社會(huì)性,人不能脫離社會(huì)而存在,人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之中,致力于社會(huì)公共秩序的改善是人的宿命。世界上只有兩種東西不需要社會(huì)性:一是超越界的神,一是自然界的畜生,人永遠(yuǎn)都不可能脫離社會(huì)性而單獨(dú)存在。但真正有活潑創(chuàng)造生機(jī)的公共社會(huì),必然是能夠尊重人的個(gè)體自由,維護(hù)人的自我選擇的權(quán)利的。但自由決非空洞無物的自由,而是充滿了仁愛精神的自由;選擇也不是遠(yuǎn)離價(jià)值的選擇,而是依據(jù)良知律令做出的選擇。無論集體性或社會(huì)性,都必須維護(hù)人的尊嚴(yán),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而不能蔑視人的尊嚴(yán),傷害人的自由意志。集體性與個(gè)體性應(yīng)該合成一個(gè)良性互動(dòng)的張力結(jié)構(gòu),必須兩邊同時(shí)兼顧,不能一頭大而一頭小。良知本體可以是超越的個(gè)體的,良知行為則是歷史的社會(huì)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顯然最大化地彰顯了人的自由意志和價(jià)值選擇,但作為人的存在選擇則必然要具體化到活生生的歷史場(chǎng)域中去,轉(zhuǎn)化為具有特殊經(jīng)驗(yàn)內(nèi)容的生動(dòng)歷史行為。我既要保持自己的獨(dú)立人格,又要維護(hù)一個(gè)民族的集體選擇,一切都以不違背無人不有的良知為根本前提,否則寧可選擇流放或殺頭。這才是提倡良知學(xué)說應(yīng)有的真義,可惜今天已為絕大多數(shù)人所遺忘。
郭萍:但是我還發(fā)現(xiàn),陽明他畢竟是為官的,他有非常多的政治業(yè)績(jī)。我們說,他思想中反專制的向度,但是現(xiàn)實(shí)中他還是忠君的,包括他平定叛亂等等,他是需要得到君王的一種認(rèn)可的。這體現(xiàn)了他思想當(dāng)中的一種矛盾,我們應(yīng)該怎么審視這個(gè)問題?
張新民:王陽明生活的時(shí)代,從政治生態(tài)學(xué)的角度看,皇權(quán)專制不能不說是達(dá)到了高峰,如果比較宋代政治的開明,尤其是知識(shí)精英群體的意氣風(fēng)發(fā),更可說是前后懸殊太大。明代皇權(quán)專制的惡化,最明顯的事件一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廢相權(quán),再即明成祖朱棣的殺方孝孺。相權(quán)一旦經(jīng)朱元璋之手廢除,內(nèi)閣首輔不過就是大秘書長(zhǎng)而已。從此君主的威權(quán)急劇膨脹,絕對(duì)專制的局面開始形成。至于朱棣殺方孝孺,不是殺一人,是滅其十族,牽取遭害的人數(shù)多達(dá)870人,釋放出來的信息不僅是殺一擁有權(quán)威號(hào)召力的大臣,更是殺一擁有文化象征意義的讀書種子,說明學(xué)術(shù)非但不能引領(lǐng)政治,反而動(dòng)輒就成為權(quán)力的犧牲品。這必然會(huì)造成士人心理上的巨大陰影,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出處進(jìn)退行為。陽明是受了廷杖才發(fā)配到貴州龍場(chǎng)的,廷杖就是朱元璋首先采用的一種惡刑。所以,明代士人隱身不仕的人很多,包括王門后學(xué)的不少重要人物。王陽明自己也是明代惡政的受害者,所謂“百死千難”更多地是與政治迫害相牽聯(lián),甚至立了功也遭遇到殺頭滅族的可能性危機(jī),他對(duì)皇權(quán)專制流弊的體會(huì)必定是深刻的。但傳統(tǒng)皇權(quán)本質(zhì)上即是國(guó)家權(quán)力的合法性象征,在國(guó)家權(quán)力合法性沒有完全喪失之前,任何忠貞耿直的行為都是正當(dāng)?shù)模覀儧Q不能用現(xiàn)代的“革命”思維來要求他反皇權(quán)。
因此,王陽明在他的官任上,當(dāng)然必須有所作為。但他的作為不是在中央朝政大局的變革上,而是在地方社會(huì)秩序的維系上;他的可以涵蓋一切人的良知學(xué)說,顯然也為收拾地方人心提供了理論依據(jù)。王門后學(xué)人物多走覺民行道的下行路線,少走借君行道的上行路線,原因固然主要是上行路線已為專制惡政所堵死,但也與陽明的良知理論特別是“親民”思想的影響不無關(guān)系。陽明后學(xué)后來有泰州學(xué)派的興起,他們更多地強(qiáng)調(diào)“百姓日用之學(xué)”,儒學(xué)平民化的發(fā)展方向十分突出,走的正是一條扎根民間和建構(gòu)秩序的道路。從王艮、顏鈞、羅汝芳這批人的身上,正好可以看到以百姓日用指點(diǎn)現(xiàn)成良知的一套具體作法。王陽明所謂“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實(shí)際己在前面做了理論先行的開頭工作。要求他們公開反皇權(quán)顯然是不現(xiàn)實(shí)的,以為他們就順著皇權(quán)討好說話也決非事實(shí)。他們的身上或多或少都表現(xiàn)出批判的精神,激烈時(shí)甚至表現(xiàn)出不與朝廷合作的態(tài)度,完全是與早已官學(xué)化的程朱理學(xué)有別的另一時(shí)代思潮,反映了民間基層經(jīng)濟(jì)和文化力量崛起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發(fā)展趨勢(shì)。
傳統(tǒng)國(guó)家的人格化形態(tài)是要以“君”來表征的,因而我們很難將“君”從國(guó)家觀念中區(qū)隔出來。忠于君與忠于國(guó)乃是一體之兩面,即使對(duì)皇權(quán)的合法性源頭喪失了信心,士人群體也不可能去反國(guó)家,作亂本身就是一種“害道”的罪名。儒家的秩序情結(jié)決定了他們的精神取向總是建構(gòu)性的,最高的理想便是恢復(fù)三代至大至公之治。以良知本體為依據(jù)展開的各體批判,本質(zhì)上也是同時(shí)兼顧揚(yáng)棄與建構(gòu)兩種精神的。如果將其作一個(gè)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化,即今天我們?nèi)杂斜匾l(fā)揚(yáng)以良知為主導(dǎo)的批判精神,就必須調(diào)動(dòng)各種資源來處理復(fù)雜的社會(huì)問題,但無論如何我們的批判依然必須是揚(yáng)棄或建構(gòu)式的,是一種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又有肯定,或者理想的層面否定、現(xiàn)實(shí)的層面肯定的《春秋》筆法的批判。我們的批判不是要將國(guó)家和社會(huì)抹黑,而是要剔除國(guó)家和社會(huì)一切可能存在的負(fù)面雜質(zhì)。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問題的確很多,但未必就沒有積極的因素,“利”與“弊”往往就在同一事物之中,批判的目的就是要將“弊”轉(zhuǎn)化“利”。泰州學(xué)派主將顏均最強(qiáng)調(diào)的便是“自我主宰無依”,他所表現(xiàn)出來的正是一種十分個(gè)性化的自由精神。如同思想應(yīng)該是獨(dú)立不倚和積極自由的一樣,我們今天的批判也應(yīng)該是獨(dú)立不倚和積極自由的。從儒家傳統(tǒng)特別是王學(xué)人物前后相續(xù)的譜系中,完全可以挖掘出大量可資利用的主體性資源和批判性資源。正像天道循環(huán)落實(shí)為四季變化必然是一個(gè)緩慢的過程一樣,化弊為利的政治批判也是一項(xiàng)必須持之以恒的長(zhǎng)期的工作。當(dāng)然,天道生生不息,不能不表現(xiàn)為萬物的活潑生長(zhǎng),正如冬天的降臨其實(shí)只是為春天的到來做準(zhǔn)備一樣,即使有凋謝、凋枯和死亡,也是為了更好地生生。天道的剛健在于其從不會(huì)停止運(yùn)作,人類求善的奮斗也永遠(yuǎn)無止境。
無論古今中外,任何一個(gè)社會(huì)都必然存在著有待其改革的問題,我們思考一個(gè)問題時(shí),任何簡(jiǎn)單的肯定或否定都是片面的。社會(huì)的發(fā)展是透過不斷調(diào)整才得以實(shí)現(xiàn)的,調(diào)整本質(zhì)上就是化弊為利,或者說將負(fù)的轉(zhuǎn)化為正的,劣的轉(zhuǎn)為優(yōu)的,然后推動(dòng)社會(huì)繼續(xù)向前發(fā)展。但社會(huì)的問題有時(shí)就像人的偏頭痛一樣,左邊剛好右邊又發(fā),調(diào)整就是在左與右之間不斷穿行,重要的是必須守往中線,也就是守住古文《尚書·大禹謨》“允執(zhí)厥中”之“中”,盡可能地避免過左、過右引發(fā)的大幅度震蕩,時(shí)刻保持化負(fù)為正的糾偏機(jī)制,才能避免社會(huì)發(fā)展的翻車出軌。真正具有批判精神的學(xué)者,更應(yīng)及時(shí)發(fā)出可能出軌翻車的時(shí)代警示,做一個(gè)敢于匡正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方向的扳道夫。這樣的工作必須調(diào)動(dòng)一切可能的積極性資源,不斷在左與右的否定過程中實(shí)視人類所要尋找的正題。而正就是中,中就是無過無不及,只有中道才是正道,否則都難免偏來倒去的惡果。當(dāng)然,偏就意味著需要調(diào)整,就像開車必須及時(shí)把握方向,不能遠(yuǎn)離了正道才事后來調(diào)偏差。根據(jù)路況的復(fù)雜也可容許一定的靈活性,但如陽明所說良知始終都是定盤針,不僅代表了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主體性,而且能夠隨時(shí)發(fā)出危險(xiǎn)的呼吁,提醒人們及時(shí)調(diào)整發(fā)展方向,避免一切步入歧途的可能性。即使我們多次談到的精神生命的安頓問題,抽掉良知亦會(huì)變得一片空無,因而無論任何調(diào)整和發(fā)展,都必須以良知的到場(chǎng)和作主為根本前提。
郭萍:您剛才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的實(shí)際發(fā)展總是或左或右的,我們需要不斷調(diào)整。那么,現(xiàn)在我們的社會(huì)里邊最大的一個(gè)弊端是什么?不管是陽明心學(xué)還是整個(gè)儒學(xué),能做什么樣的調(diào)整?
張新民:如果我們回顧1949年以后中國(guó)社會(huì)的發(fā)展,不必列舉很長(zhǎng)的時(shí)段,就是所謂前后兩個(gè)30年,就會(huì)發(fā)現(xiàn)總是存在或左或右發(fā)展上的偏差。作為充滿著問題走過來的一代人,不僅在國(guó)家民族傷痛的記憶上,而且更在文明野蠻退墮的憂患上,我想我們是有足夠的批判發(fā)言權(quán)的。
不妨先看前30年,國(guó)家政策始終擺脫不了極左的封閉形態(tài),所謂“寧要社會(huì)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和平時(shí)期居然餓死了幾千萬人,以為可以用解決人的精神問題方法來解決人的物質(zhì)問題,物質(zhì)的匱乏可以說是到了極點(diǎn),以致到80年代初我自己都還有饑餓感。老百姓饑餓,宣傳上卻一片光明,好像經(jīng)濟(jì)發(fā)展滯后的危機(jī)從來就不存在,不是偏到一頭是什么呢?至于后30年,經(jīng)濟(jì)是發(fā)展了,物質(zhì)不再匱乏了,但貧富差距也拉大了,認(rèn)同也分裂了,只講物質(zhì)不講精神的危機(jī)出現(xiàn)了,是不是又偏到了另一頭呢?總結(jié)前后30年,我們是不是該著眼于華夏民族的整體福祉,以左顧左盼的方法來尋找一條新的道路,亦即通過無過不及的合理化中道,來更好地為中國(guó)的未來謀求發(fā)展呢?
現(xiàn)在最大的問題是,從上到下,一個(gè)民族應(yīng)有的氣節(jié)精神垮掉了。物質(zhì)生活不可否認(rèn)是極大地提高了,但諸如信仰迷失、價(jià)值混亂、意義困惑、道德淪喪一類的問題也出現(xiàn)了。昨天我看到一個(gè)消息,說美國(guó)奧巴馬政府執(zhí)政期間,沒有修一公里的高速路;而同一時(shí)期的中國(guó)政府,則修了2萬公里的高速路。現(xiàn)在美國(guó)的基礎(chǔ)設(shè)施都落后于我們了,但我們能自夸當(dāng)下的中國(guó)人的素質(zhì)就遠(yuǎn)高于美國(guó)人嗎?一個(gè)物質(zhì)上強(qiáng)大了的中國(guó),精神上也強(qiáng)大了嗎?傳統(tǒng)中國(guó)是禮義文明之邦,現(xiàn)在還能這樣自豪地宣稱嗎?精神和物質(zhì)作為兩個(gè)世界,是不是應(yīng)該平衡發(fā)展,又應(yīng)該如何平衡發(fā)展?我以為這是大家都應(yīng)該思考的問題。另一個(gè)問題是精神世界如果要與物質(zhì)世界平衡發(fā)展的話,它的本體依據(jù)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缺少了真實(shí)人性的支撐,精神世界能夠建構(gòu)起來嗎?建構(gòu)的基礎(chǔ)如果是虛無飄渺的烏托邦,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老百姓又有什么意義呢?
要回答或解決以上問題,傳統(tǒng)儒家的不少經(jīng)驗(yàn)是可以借鑒的。例如,自先秦以來,儒家就強(qiáng)調(diào)“先富之,后教之”,富裕固然是發(fā)展的基礎(chǔ),但富裕之后的教化也不忽視。至于“上下交征利而國(guó)危矣”、“國(guó)不患寡而患不均”一類的古訓(xùn),不能說完全沒有影響到古代帝國(guó)的實(shí)際決策,今天仍有必要將其轉(zhuǎn)化為糾偏機(jī)制的合理理論資源。重要的是必須有一形上本體的深厚扎根,不能丟掉人心民意的廣泛認(rèn)同,包括孔孟推己及人恕道精神的重新發(fā)揚(yáng),陽明良知學(xué)說實(shí)戰(zhàn)化的制度安排。華夏民族幾千年文明積累的經(jīng)驗(yàn)資源是很豐富的,任何時(shí)候的挖掘都不可能是空手而還。
如果今天仍然要將過去或左或右的政策固定化,喪失了依據(jù)中道隨時(shí)調(diào)整損益的靈活性,
遺忘了《易經(jīng)》所謂變則能通的應(yīng)變能力,前面留下的負(fù)面遺產(chǎn)不僅不能及時(shí)清理或消解,反而有可能以變形的方式再度滋生和蔓延,這是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應(yīng)該警惕和防范的。1949年到現(xiàn)在60多年的發(fā)展經(jīng)驗(yàn),必須置于五千年文明嬗蛻的長(zhǎng)河來作審思和判斷,否則便難免不會(huì)患上短視病或夜盲癥,因?yàn)椴恢缽哪抢飦硗鸵馕吨恢赖侥抢锶ァ@纾馗挥诿襁€是藏富于國(guó)一類的問題,傳統(tǒng)中國(guó)就有過不止一次的討論;儒家的理財(cái)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討論問題的深度和廣度也極為可觀,即使置于世界之林也當(dāng)大放光彩。古典的智慧未必就不能對(duì)治現(xiàn)代性的病癥,一切都取決于當(dāng)今人類有無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造的能力。當(dāng)然,如同尊重歷史并非就是要停留在歷史之中一樣,理解現(xiàn)實(shí)也并非就是要維護(hù)現(xiàn)實(shí),一切合理的謀劃都必須著眼于未來的發(fā)展,批判的意識(shí)和開新的精神任何一邊都不能缺少。擴(kuò)大思想的空間與拓寬發(fā)展的可能應(yīng)該是同步的,歷史和現(xiàn)代兩重眼光交叉互審互視,同時(shí)更加具備前瞻性的睿智,今天看來就尤其顯得重要。例如,陸象山與譚嗣同,兩人一先一后,都講“沖破羅網(wǎng)”,“羅網(wǎng)”是什么?羅網(wǎng)就是一切束縛人的成見或偏執(zhí),無論文化心理的或客觀現(xiàn)實(shí)的,無形的或有形的,除了天道、人性、良知及其客觀化的規(guī)范外,一切人為的異化的束縛都應(yīng)該統(tǒng)統(tǒng)打破。天道決定了人必須跟自然和諧相處,人道本質(zhì)上就是天道,二者以活潑創(chuàng)進(jìn)或生息不已為根本。我們只有立足于天道、人性、良知三者合為一體的完整世界,積極展開歷史性思考和合法性批判,才能形成上下左右縱橫交錯(cuò)的立體性審視眼光,從而最大化地調(diào)動(dòng)一切可資利用的資源,引領(lǐng)社會(huì)風(fēng)氣朝著合理健康的方向有序地變遷發(fā)展。
郭萍:最近30年,精神信仰的問題凸顯出來了。特別是近十幾年來,國(guó)家層面也意識(shí)到這個(gè)問題,所以開始重視傳統(tǒng)文化的復(fù)興、儒學(xué)的復(fù)興。但是,我們也發(fā)現(xiàn)在儒學(xué)復(fù)興的大背景下,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儒學(xué)理論,其中一些儒者更愿意直接談制度建構(gòu),而不談本體論,也提出“政治儒學(xué)”與“心性儒學(xué)”的區(qū)分。但剛才您談到的,社會(huì)制度的建構(gòu),包括人心的安頓、道德的重塑等等各種問題,還是需要一個(gè)本體論依據(jù)的。您對(duì)這種狀況怎么看?
張新民:“政治儒學(xué)”與“心性儒學(xué)”是不是應(yīng)該區(qū)隔為兩橛,古典儒學(xué)世界根本就沒有產(chǎn)生過這類問題,包括后來的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復(fù)觀等現(xiàn)當(dāng)代新儒家,他們固然更多地關(guān)注心性之學(xué),但未必就沒有自己的政治關(guān)懷。只是他們要從心性之學(xué)開出來的,依然是西方的科學(xué)和民主,實(shí)際與全盤西化派的政治訴求沒有太大的區(qū)別。他們與西化派的對(duì)立主要是文化立場(chǎng)上的,即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是否對(duì)立的問題上,相互之間有著絕然不同的觀點(diǎn)或看法,要害仍然是要不要徹底否定中國(guó)文化。
心性儒學(xué)與政治儒家的關(guān)系,在傳統(tǒng)儒學(xué)的語境之中,更多地是以“內(nèi)圣”與“外王”兩個(gè)范疇來加以表述的。從歷代大儒的視域出發(fā),二者從來都是一體之兩面,代表了人及其所處的社會(huì)不或缺的兩個(gè)發(fā)展向度,是決然不能割裂為互不相關(guān)的兩個(gè)部分的。我們看孔子贊嘆:“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舜與禹在孔子心目中,顯然就是“內(nèi)圣”與“外王”合一的人間典范,代表了人格與事業(yè)融然合為一體的一種存在方式,完全可以用“圣王”兩字來加以概括或指稱。這當(dāng)然也為后世的儒家提供了批判的思想資源,因?yàn)樵谥熳右活惖娜彘T學(xué)者看來,三代以下的帝王統(tǒng)統(tǒng)都是私心治天下,后世的王朝政治都不是理想的政治,所以他們必須以道統(tǒng)來匡正政統(tǒng),即使帝王也必須告誡其不能放廢正心誠(chéng)意的修身工夫,否則就意味著喪失了儒家的身份和價(jià)值立場(chǎng),步入了法家只講“外王”不講“內(nèi)圣”的歧途。
不過,就個(gè)人的研究興趣和具體的人文關(guān)懷而言,當(dāng)然可以容許有心性儒學(xué)或政治儒學(xué)的好尚與選擇的。然而一旦將儒學(xué)價(jià)值引入政治領(lǐng)域,二者仍不能割裂為互不關(guān)涉的兩橛。難道我們?cè)趶?qiáng)調(diào)治國(guó)平天下的重要性的同時(shí),能夠放棄官員修身自律的要求嗎?政治本質(zhì)上即是人的政治,涉及多數(shù)人的利益和福祉,不能不有人的整個(gè)生命或人格的自覺性投入,必須有與人的“四端”之心直接相關(guān)的仁、義、禮、智的真實(shí)到場(chǎng),否則不僅會(huì)造成政治的虛假或偽善,而且也會(huì)減少社會(huì)輿論監(jiān)督或批判的壓力,反而違背了儒家不允許政治領(lǐng)域出現(xiàn)價(jià)值真空的初衷。無論任何時(shí)候,我們都不能容忍政治是由小人而非君子組成的世界,制度安排則從選拔、任用、監(jiān)督、考查、彈劾、罷黜等一系列環(huán)節(jié),都要有相應(yīng)的獎(jiǎng)懲結(jié)合的具體方法或措施,形成一種民間清議與制度安排結(jié)合的近君子、遠(yuǎn)小人的良好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
大陸新儒家為彌補(bǔ)港臺(tái)新儒家只講心性學(xué)的不足,重新從《五經(jīng)》特別是《春秋》公羊?qū)W中挖掘思想資源,重建與其有別的政治儒學(xué)。我以為二者之間不是相互對(duì)立或否定的關(guān)系,恰好可以以此為基礎(chǔ),舉凡心性儒學(xué)所缺失者,正好政治儒學(xué)可以來彌補(bǔ),以強(qiáng)化其較為欠缺的“外王”面;政治儒學(xué)所缺失者,恰好心性儒學(xué)也能從中彌補(bǔ),以深化其較少涉及的“內(nèi)圣”面。這樣才能更好地為未來儒學(xué)的綜合創(chuàng)造發(fā)展做好先期的思想積累工作。即使二者暫時(shí)不能有效整合,我們也可以憑借心性儒學(xué)來“守道”,依據(jù)政治儒家來“行道”,“守道”與“行道”根據(jù)具體政治語境而展開,是完全可以做到并行而不悖的。
儒家要獲得新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就不能不回應(yīng)當(dāng)下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例如,現(xiàn)在西方的民主的確問題很多,只能稱為經(jīng)常令人感到遺憾的最不壞的政治,并非人類所尋找的更理想更完美的制度的終結(jié)。我們看美國(guó)最近的大選,希拉里與特朗普互揭對(duì)方的隱私,在儒家看來就是極不道德的,我們是不是可以超越西方的民主制度,找到一種更少弊病而又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但是,我們?cè)谂u(píng)西方的民主制度時(shí),并非就意味著我們回避現(xiàn)行中國(guó)政治制度存在的問題,我們只是想尋找有更多人類經(jīng)驗(yàn)支撐的合理制度架構(gòu),挖掘更多的重建新型制度必需的合法性資源,在更高的層面上實(shí)現(xiàn)儒家一貫重視的德性政治和人性化制度。這顯然是對(duì)人類智慧的考量。既然是關(guān)注人類的整體經(jīng)驗(yàn),為什么要將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排除在外呢?中國(guó)畢竟有五千年國(guó)家經(jīng)營(yíng)和管理的經(jīng)驗(yàn),為什么不可以首先依據(jù)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坦率陳言,同時(shí)又以此基礎(chǔ)提煉天道性理的理想化衡量標(biāo)淮,做出超越西方的合理性制度設(shè)計(jì)和安排呢?
心性儒學(xué)和政治儒學(xué)之所以不可分,更重要的一層原因是:我們不僅希望個(gè)人是理性的和道德的,同時(shí)也希望國(guó)家是理性的和道德的,正義的個(gè)人與正義的國(guó)家,或者說修身以治心跟修身以治世,二者之間應(yīng)該是一體的,任何一個(gè)方面的缺位都是不允許的。王陽明代表了傳統(tǒng)心性學(xué)發(fā)展的高峰,但也兼有三不朽的事功,說明心性之學(xué)與外王之是可以統(tǒng)一起來的。他平定朱宸濠叛亂以后,以有身之功蒙受冤屈而終于平反,大家都以為他功勛卓著, 他卻認(rèn)為一旦圣人“得位行志”,必然能夠?qū)?zhàn)爭(zhēng)禍亂消弭于未形之際,而他自己則在戰(zhàn)爭(zhēng)禍亂已形成之際用兵,亦即是在禍亂已產(chǎn)生的“半中截”做事,與在根源上就將禍亂消歸于無形有著天壤之別。在他看來治國(guó)如同治病,不僅要在病癥已發(fā)后及時(shí)施藥,更重要的是在病癥未發(fā)時(shí)便已獲得有效防治。病象盡管在社會(huì),病根卻在人心。如何在病癥未發(fā)時(shí)即獲得有效防治呢?當(dāng)然必須深入心源做省察克治的工夫,在動(dòng)機(jī)世界就軋斷了禍亂發(fā)生的可能性源頭。外在有形的他律性社會(huì)治理固然重要,內(nèi)在無形的自律性修心工夫也不能忽視。這是將心性學(xué)引入政治場(chǎng)域,從根本上扶持國(guó)家社會(huì)所必須的浩然正氣,從源頭上鏟除積累己深的政治流弊,決非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式的內(nèi)病外治可比,可說是強(qiáng)本固根、扶正祛邪的外病內(nèi)治方法的發(fā)揚(yáng),足以說明心性儒學(xué)與政治儒學(xué)的不可二分。只有法治與德治一起抓,既治末又治本,道德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有可能實(shí)現(xiàn)儒家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
從儒家的歷史貢獻(xiàn)看,通過“上行”、“下行”兩條價(jià)值發(fā)展方向上的互動(dòng),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很早便建立了一個(gè)范圍廣大的教化體系。這個(gè)教化體系廣涉修身倫理、家庭倫理、社區(qū)倫理、國(guó)家倫理、天下倫理,一端始終聯(lián)系著個(gè)人,不能離開個(gè)人的心性體認(rèn)工夫,一端則長(zhǎng)期聯(lián)系著天下,總是滿懷蒼生百姓關(guān)懷,不僅說明個(gè)人的存在價(jià)值和意義可以層層向外推廓擴(kuò)大,而且反映人人可在其中受到心志情操的教化熏陶。透過這個(gè)教化體系多種多樣的輸入渠道,儒家整體而全面地傳播和落實(shí)了自己所要推廣的各種價(jià)值,充分地發(fā)揮了從國(guó)家到基層上下貫通的治理功能。以個(gè)人修身為起點(diǎn),直接通貫到天下國(guó)家,也反映了個(gè)體性與集體性的巧妙整合;無論任何復(fù)雜廣大的社會(huì)治理空間,都不能將個(gè)體人及其所必須的道德品質(zhì),從中抽離剝落出去。
傳統(tǒng)中國(guó)的心性之學(xué),既是一種德性形上學(xué),又是一種宇宙形上學(xué),雖最為關(guān)注人類社會(huì),但又并非人類中心主義,是宇宙人生一氣貫通的。因而整合心性儒學(xué)和政治儒學(xué),必然有助于政治儒學(xué)深挖人性與天道的形上資源,從而建構(gòu)起一套系統(tǒng)性的政治形而上學(xué)。心性儒學(xué)所講的心性,當(dāng)然也不會(huì)自我封閉起來,必然在修養(yǎng)和證量上展現(xiàn)其全體大用,汲汲于謀求政治制度合法性問題的解決,必然能夠與政治儒學(xué)會(huì)通對(duì)接。一旦心性封閉而不能開通,人就只能變成一堆死肉,即使佛教也不可能將心性封閉起來,否則如何解釋能夠轉(zhuǎn)識(shí)為智成佛?怎樣解釋一念凈即國(guó)土凈,一念染即國(guó)土染,心的凈染亦關(guān)系到自己所要交往的世界的凈染,終極性的價(jià)值向往仍是心與涅槃解脫世界的連接。儒家以天下百姓的憂樂為自己心中的憂樂,當(dāng)然就要時(shí)時(shí)防范和克治自己的自私或狹隘,將心量開放到與整個(gè)浩渺太虛同體的程度,才能實(shí)現(xiàn)自己一貫主張的成己成人乃至成物之學(xué)。
因此 儒家的心性之學(xué)是一定要通出去的,通則必然與政治制度的建構(gòu)活動(dòng)相發(fā)生密切關(guān)聯(lián),否則人心不到場(chǎng),良知不到場(chǎng),即意味著價(jià)值不到場(chǎng),天理不到場(chǎng),政治建構(gòu)活動(dòng)又如何開展呢?在這一意義上,我認(rèn)為心必須四面八方打通,不僅要與橫向的生活世界、政治世界打通,而且更要與形上世界、超越世界打通,分之則可以是認(rèn)知心,道德心、智慧心、超越心,合之則不過是充滿了價(jià)值與意義的完整而開放的心而已。這顯然是人的主體性的最大化發(fā)揚(yáng),不能不涉及多方面的政治制度建構(gòu)活動(dòng),包括大家關(guān)心的民主制度的建構(gòu)活動(dòng),不是要否定它,而是要超越它,只有超越才能重建人人都擁有尊嚴(yán)和自由的禮樂典章文明制度。所以,我認(rèn)為我們不能過多強(qiáng)調(diào)大陸新儒家與港臺(tái)新儒家的對(duì)立,只有以包容的心態(tài)來謀求綜合性的發(fā)展,然后各自做出能對(duì)治現(xiàn)實(shí)問題的多方面的學(xué)理安頓,才能真正彰顯出儒家的大圓融睿智。如同唐君毅所說,過去的中國(guó)文化花果飄零,他們的工作主要是為其辯護(hù)和正名;今天的中國(guó)文化已經(jīng)開始抽芽發(fā)枝,我們的工作主要是推動(dòng)其繁榮興盛。這樣的工作一代接著一代做下去,如同港臺(tái)新儒家一樣,我們也是過渡時(shí)代的過渡人物而已。政治制度的安排應(yīng)當(dāng)容許有各種設(shè)計(jì),不能滿足于現(xiàn)行制度的一成不變,有分歧意見不能說不是正常現(xiàn)象,但要盡可能地尋找各家各派最底限度的共識(shí),避免社會(huì)認(rèn)同撕裂可能導(dǎo)致的解體危機(jī)。大陸政治儒學(xué)的制度關(guān)懷反映了中國(guó)人當(dāng)下的存在焦慮,批評(píng)、爭(zhēng)論、反駁等等都是正常的現(xiàn)象,但他們的制度關(guān)懷本質(zhì)上仍順應(yīng)了變革的時(shí)代潮流,當(dāng)然不應(yīng)該以打棒子的方式輕易地就加以否定。
郭萍:您特別強(qiáng)調(diào)心并不是純粹封閉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它需要跟現(xiàn)實(shí)世界打通。那反過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即便是要進(jìn)行現(xiàn)在很現(xiàn)實(shí)的制度化的建構(gòu),也需要有一個(gè)本體論的支撐或者是一個(gè)集聚。在這個(gè)方面,我們?nèi)绻_展政治儒學(xué),是不是要在個(gè)方面還要繼續(xù)加強(qiáng)一些?
張新民:是要加強(qiáng),因?yàn)橐粋€(gè)時(shí)代有一個(gè)時(shí)代的問題,
我們要加以解決就必須耗費(fèi)大量的心智和精力,也會(huì)成為大眾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或熱點(diǎn)。今天我們追問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問題,也必須凝聚起心中的理性和智慧,調(diào)動(dòng)一切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思想資源,以求獲得有利于問題解決的突破性路徑。任何政治制度的存在都是不能反人性的,同時(shí)也是不能反文化的,它是在幾千年文明系統(tǒng)積累發(fā)展的基礎(chǔ)之上建構(gòu)起來的,文明系統(tǒng)的存在又是與生活世界的存在一體的,是民族集體共同經(jīng)營(yíng)和創(chuàng)建的。因此,我們也不能一廂情愿地放大自己理性設(shè)計(jì)或安排的重要,以為單靠自己的理性設(shè)計(jì)或安排即可改變歷史性存在的既有制度。例如,“文化革命”中連春節(jié)都不能過,自己拜自己的祖宗都不行,這其實(shí)就是一種反文化的愚蠢行為。文化的世界本質(zhì)上就是生活的世界,所以反文化本質(zhì)上就是反老百姓。可見任何制度的建構(gòu)活動(dòng)都必須從歷史文化中尋找誘變的動(dòng)因,不能憑空想象地強(qiáng)加或生搬硬套地移植。國(guó)家本身就是神圣與世俗的綜合體,只是管理國(guó)家必須有政府,政府的受權(quán)不能憑空而來,當(dāng)然就需要從形上、形下兩個(gè)方面尋找合法性或正當(dāng)性,必須獲得天道性理及人心民意雙重價(jià)值上的支撐。談到形上則必然涉及人性與天道,必須對(duì)神圣的天道和人性懷抱敬意和責(zé)任,難道我們能設(shè)想制度的存在是反人性、反天道的嗎?講到形下也會(huì)牽聯(lián)人的歷史經(jīng)驗(yàn)和生活世界,必須對(duì)世俗民眾的生存、生活、勞作和信仰滿腔的關(guān)心和同情,難道制度的存在能違背或脫離人的歷史經(jīng)驗(yàn)和生活世界嗎?任何政治權(quán)力只能服從天道,不能僭越天道,只能尊重民意,不能強(qiáng)奸民意;只能直面歷史,不能篡改歷史。生活世界是安立于天地之間的, 除了生活世界本身的歷史性維度可以提供價(jià)值外,天地生生不息的創(chuàng)化力量本身也是一種價(jià)值,當(dāng)然就應(yīng)該構(gòu)成人與天地合其德的正當(dāng)性目的訴求,陽明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nèi),直造先天未畫前”,實(shí)際已看到了形上與形下兩個(gè)世界的不可分離。因此,一方面“百姓日用即是道”,普通日常的生活也有形上的意義,為政者必須時(shí)時(shí)刻刻做到陽明所倡導(dǎo)的“親民”;另方面“圣人之道無無異百姓日用”,形上的意義就寄寓于普通日常的生活之中,為政者必須隨時(shí)隨地以自己的行為典范來施行儒家所倡導(dǎo)的“教化”。政治制度作為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的一種工具或手段,必須在形上與形下兩方面都彰顯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與正當(dāng)性。
正當(dāng)性與合法性的自我行為證明,必須是政治活動(dòng)無條件接受的選項(xiàng),否則“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丟失了正當(dāng)性與合法性的政府,當(dāng)然是不能為人民接受的。儒家所說的天道性理是一氣貫通的,我們不需要安排西方一神教的上帝,但同樣可以透過超越與世俗兩個(gè)層面的良性互動(dòng),全面有效地安排好我們的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如同天道是自然現(xiàn)象世界的隱性秩序存在,自然現(xiàn)象世界則是天道的顯性秩序存在一樣,人的心靈也是社會(huì)政治文化生活的隱性秩序存在,社會(huì)政治文化生活同樣即是人的心靈的顯性秩序存在。人的心靈的隱性秩序與天道的隱性秩序是一體不二的,所以政治文化生活秩序跟自然現(xiàn)象秩序也應(yīng)該是和諧一致的。無論天道的秩序化運(yùn)作或心靈的秩序化展開,都要求我們必須建立一個(gè)能維護(hù)人的生命尊嚴(yán)和生活福祉的良好政治文化秩序,二者之間必須是通而不隔的,可以說成是人天一體的。人天一體即意味著人文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文化,人文的秩序結(jié)構(gòu)與自然的秩序共同合成了創(chuàng)進(jìn)不已的生命交響曲。正因?yàn)槿绱耍覀儾攀冀K關(guān)心政治制度的建構(gòu)活動(dòng),希望它朝著良性的方向健康發(fā)展,做到心靈、社會(huì)、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秩序的互相呼應(yīng),任何一方面出現(xiàn)問題都要補(bǔ)弊糾偏,不能用一個(gè)方面去壓抑另一個(gè)方面,否則都有可能扭曲錯(cuò)位或變形異化。這是中國(guó)發(fā)展的大方向,盡管困難重重難,但大家同舟共濟(jì),前景仍然是光明的。
郭萍:您說在這個(gè)意義上,就我們現(xiàn)在現(xiàn)代中國(guó)人的主體性而言,還沒有完全建構(gòu)起來,是不是這樣的呢?
張新民:是沒有建立起來,譬如我們能說全中國(guó)人民都是國(guó)家政治生活的主人翁嗎?如果是主人翁,請(qǐng)問參與的渠道在哪里呢?民間下層社會(huì)與上層權(quán)力社會(huì)上下流動(dòng)的空間徹底敞開了嗎?如果沒有徹底敞開,堵塞的原因是什么呢?富起來的中國(guó)人其實(shí)問題是很多的,一個(gè)大寫的中國(guó)人還有一個(gè)過程才能真正挺立起來。
不過,文化的建設(shè)是不能犯急躁病的,前人認(rèn)力“文王積徳百年,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后大行”。可見文化建設(shè)是一步步發(fā)展和擴(kuò)大起來的。經(jīng)濟(jì)建設(shè)60年就上去了,成為第二大經(jīng)濟(jì)實(shí)體了,道德建設(shè)也能這樣成倍翻番嗎?文化建設(shè)是每一個(gè)人都可參與的事,取決于每一個(gè)人當(dāng)下的努力,不能不有當(dāng)下的主體精神的發(fā)揚(yáng)。即使是政治儒學(xué),也必須有人的主體性參與。任何實(shí)踐活動(dòng)都不能將人從中剝離出來,好的文化加上好的制度,確保人人都能透過實(shí)踐挺立起自己的主體人格,才構(gòu)成一個(gè)可以讓民族集體安身立命的完整世界。
郭萍:您認(rèn)為這個(gè)時(shí)代我們講良知是人人都有的,都應(yīng)該挖掘出來的,那是不是就是每個(gè)人都應(yīng)該有這樣的一種擔(dān)當(dāng),去參與到社會(huì)政治制度的建構(gòu)、人格的塑造里邊來,而不是僅僅像以前那樣的,僅僅是屬于士大夫階層或者精英階層的事情,而是所有每一個(gè)人的事情。
張新民:對(duì)!今天的政治制度建構(gòu)活動(dòng),不應(yīng)該是封閉的不透明的,而只能是開放的敞亮的,如同市場(chǎng)的開放促進(jìn)了資源的流動(dòng)和配置一樣,政策的開放也應(yīng)該促進(jìn)人才的流動(dòng)和配置。只有不斷擴(kuò)大人、財(cái)、物自由流動(dòng)的空間,社會(huì)才會(huì)出現(xiàn)繁榮發(fā)展的生機(jī)和活力。我們既然開放了市場(chǎng),為什么不在政治上也開放呢?中國(guó)人的生活實(shí)踐和神感妙應(yīng)的心靈,難道不能開拓出自己廣袤的價(jià)值世界嗎?人民參與度的高低是衡量一個(gè)社會(huì)進(jìn)步與否的標(biāo)志,即使建設(shè)性的批評(píng)也是參與熱情提高的一種表示。否則一切都封閉起來,市場(chǎng)凝固了,社會(huì)僵化了,政治板結(jié)了,國(guó)家能有希望嗎?人民能有前途嗎?天下長(zhǎng)治久安可能嗎?
社會(huì)和政治的開放和平等,實(shí)際即意味著機(jī)會(huì)的開放和平等。我說的平等是機(jī)會(huì)的平等而非結(jié)果的平等,是道德的平等而非分工的平等,與其稱為制庋原則,不如說是道德原則。因?yàn)橄蛞磺腥碎_放的平等性機(jī)會(huì),必然有利于人的自由選擇和人的才情的最大化發(fā)揮,如同市場(chǎng)自由能導(dǎo)致物盡其流一樣,社會(huì)的開放也能導(dǎo)致人盡其才。開放的市場(chǎng)能夠更好地配給物質(zhì)資源,文化資源、政治資源、思想資源的配給是不是也應(yīng)該有一個(gè)開放的空間呢?傳統(tǒng)科舉制度是向一切人開放的,今天的政治用人空間是不是也應(yīng)向一切人開放呢?選拔的標(biāo)準(zhǔn)當(dāng)然只能是“賢”與“能”,這就必須有一種“德”與“位”配的制度化安排。一個(gè)縣長(zhǎng)的位置可能會(huì)影響幾十萬人的發(fā)展,因而任何一個(gè)選官的環(huán)節(jié)都必須是嚴(yán)格而公正的,僅僅是事后的消極反腐顯然是不夠的,無論事前或事后都應(yīng)該有嚴(yán)格的淘汰機(jī)制。從起點(diǎn)的公平到結(jié)果的分殊,都以社會(huì)開放所形成的自然生成機(jī)制為根本原則。只有在自由開放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中,我們才能更好地整合各種差異性的地方性知識(shí),加快族群與族群之間的交流性融合,實(shí)現(xiàn)范圍更大的民族國(guó)家的自我認(rèn)同,再造仁義禮樂形態(tài)的華夏新文明,掌握文化價(jià)值的自主性及與之相應(yīng)的話語權(quán)。面對(duì)平等開放的文化交流環(huán)境,能夠高高在上君臨天下的,只能是我們共同的道德法庭,任何人在那里都必須接受兩種批判:自我的良知拷問和永恒的歷史審判。
郭萍:您對(duì)陽明心學(xué)理解與我們當(dāng)下的生活結(jié)合的很緊密。一個(gè)儒者永遠(yuǎn)都是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具有一個(gè)天下家國(guó)的情懷。您講的從良知對(duì)于人心的安頓,一直講到我們現(xiàn)代政治制度的建構(gòu),講到政治資源的匹配,這其實(shí)能看出陽明心學(xué)對(duì)中國(guó)人現(xiàn)代主體性的建構(gòu)具有某種啟蒙意義。而您的名字叫新民,這里面也有大學(xué)問。
張新民:是的,我的名字就來自《大學(xué)》,但是那時(shí)候——我是1950年出生的——父親對(duì)外講是新民主主義的“新民”,實(shí)際卻是“大學(xué)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新民”。這也是我的一種“天命”,不能不說是代表了生命承擔(dān)的一種歷史當(dāng)然性。
剛才講到,心性儒學(xué)也好,政治儒學(xué)也好,其實(shí)真正的儒者都必須在出處進(jìn)退上把持好自己,所以歷代真正的大儒,他們無不具有卓磊超拔的人格情操,表現(xiàn)出宏闊遠(yuǎn)大的文化建構(gòu)精神氣派。認(rèn)知好自己,把持好自己,才能更好地認(rèn)識(shí)世界,改造世界,做到轉(zhuǎn)世而不被世轉(zhuǎn),沒有這個(gè)前提是不行的。我們必須在這兩方面都開拓出很大的氣象格局,才能把握好中國(guó)文化道路未來的發(fā)展方向。所以無論怎樣區(qū)分心性儒學(xué)與政治儒學(xué),良知的開顯都應(yīng)該是共同接受的觀念。
郭萍:我想這也正是孔子講的為己之學(xué)。期待有機(jī)會(huì)再與您請(qǐng)教,謝謝您!
張新民:不客氣!
版權(quán)聲明:本文內(nèi)容由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自發(fā)貢獻(xiàn),本站不擁有所有權(quán),不承擔(dān)相關(guān)法律責(zé)任。如果發(fā)現(xiàn)本站有涉嫌抄襲的內(nèi)容,歡迎發(fā)送郵件至 [email protected]舉報(bào),并提供相關(guān)證據(jù),一經(jīng)查實(shí),本站將立刻刪除涉嫌侵權(quán)內(nèi)容。
標(biāo)簽:
相關(guān)文章
北方的旅游景點(diǎn),總是能夠讓人心馳神往,在這片廣袤而神秘的土地上,藏著無數(shù)讓人流連忘返的美景。每到一處,都是一段別樣的旅程,帶給人們別樣的感受與啟發(fā)。正如李白所言:“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fēng)流人物。”……
2024-07-11
1. 金寨到合肥坐汽車要幾個(gè)小時(shí) 駕車路線:全程約262.4公里 起點(diǎn):金壇市 1.金壇市內(nèi)駕車方案 1) 從起點(diǎn)向正西方向出發(fā),行駛120米,左轉(zhuǎn)進(jìn)入華陽南路 2) 沿華陽南路行駛260米,右轉(zhuǎn)進(jìn)入金壇大道 3) 沿金壇大道行……
2024-06-28
中國(guó)古典園林的意境,一直是中國(guó)古典園林愛好者依以區(qū)別西方古典園林并且引以為豪的主要特征。何謂意境,也很難一個(gè)確切的定義,只要對(duì)中國(guó)詩詞書畫有些領(lǐng)悟的人,大多心里會(huì)有幅“意境”的圖譜。中國(guó)古典園林與西……
2024-09-29
五月西安的櫻桃大部分都已經(jīng)成熟了,那么在哪里有可以采摘櫻桃的地方呢?下面就為大家推薦了幾處可以體驗(yàn)親自采摘樂趣的好去處,很適合親子游,詳情見正文。 一、白鹿原櫻桃谷 白鹿塬北坡的櫻桃谷,這里北臨灞河……
2024-06-15
在山西有很多的遺留下來的晉商大院都是非常出名的,其中可能就是渠家大院的名氣會(huì)稍微的低一點(diǎn)。其實(shí)渠家大院的歷史是非常悠久的,近期渠家大院還將重新進(jìn)行打造,以下就是2024渠家大院門票優(yōu)惠政策。 2024山西……
2024-05-29
1. 東湖港門票加漂流多少錢 東湖港門票 成人票:50元 兒童票:25元 其他優(yōu)惠:不夠1.4米免費(fèi),學(xué)生持學(xué)生證半價(jià)。 東湖港自然風(fēng)景區(qū),位于北京房山世界地質(zhì)公園十渡園區(qū)十五渡,與野三坡毗鄰,距市區(qū)106公里,是……
2024-11-01

最新資訊
成人本科報(bào)名時(shí)間2024 報(bào)考流程是什么
150分的大專學(xué)校 150分的專科學(xué)校有哪些
山東成人高考報(bào)名流程圖 報(bào)考步驟有什么
2024山東高考大學(xué)錄取通知書什么時(shí)間能下來 發(fā)放時(shí)間幾號(hào)
云南體育生可以報(bào)考的大學(xué)
云南2024年成人高考報(bào)名入口及網(wǎng)址 報(bào)考官網(wǎng)在哪
2024河南高考大學(xué)錄取通知書什么時(shí)間能下來 發(fā)放時(shí)間幾號(hào)
廣東成人高考報(bào)名考試流程有哪些
江蘇2024年成人高考報(bào)名入口及網(wǎng)址是什么
口腔專科學(xué)校有哪些好學(xu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