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當山旅游門票,武當山旅游門票如何買
武當山旅游門票是通往武當山探訪的必備“通行證”。想必許多人都曾懷著探尋武當山的美麗與奧秘的向往,而購買門票,便是實現這一向往的第一步。武當山旅游門票如何購買?或許這個問題曾讓你迷茫,但通過這篇文章的……
2024-0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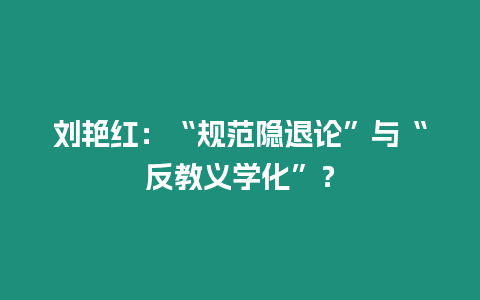
內容提要:形式法治與法教義學具有密切關聯,后者是保障前者實現的基本工具和技術力量。規范隱退論破壞了法治的最低形式限度,也是對法教義學的背離。刑法領域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正是規范隱退論與反教義學化的典型代表。如何處理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一直以來是我國刑事立法與司法關注的重點,該問題經歷了無罪論到有罪論的發展變化與理論爭議。然而,有罪論既是對刑法規范的消解,也是對刑法教義學奉現行刑法規范為圭臬之主旨的違背,它破壞了形式法治的安定性,遷就了功利主義卻拋棄了規則主義,滿足了實用主義但違背了法實證主義。根據中國刑法所采取的大陸法系國家“法人實在論”,既然“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的立法模式確立了追究單位刑事責任的刑法規范依據,因而“法律沒有規定單位犯罪則不應當負刑事責任”成為必然的結論。在中國法治建設過程中,必須確保形式法治至上,并確立法教義學的基本視角。
關 鍵 詞:規范隱退(論) 法教義學 單位犯罪 有罪論 無罪論 形式法治 Retrogression of Legal Norms Legal Dogmatics(Rechtsdogmatik) Unit Crime Theory of Guilt Theory of Innocence Formal Rule of Law
罪刑法定既是刑法的帝王原則,也是刑法教義學中的帝王教義。原則理應遵守,教義必須服從,“教義就是聽從,根據立法者”的意思。①對于單位犯罪,我國刑法第30條明確規定“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才“應當負刑事責任”。刑法明文規定單位可以作為犯罪主體成立的犯罪是為單位犯罪;其他刑法規定只能由自然人構成而單位不能成為犯罪主體的犯罪,如果現實中單位實施了,比如盜竊罪、信用卡詐騙罪等,則為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為行文簡約,本文將法無明文規定而現實中單位實施了的犯罪稱為非單位犯罪,必要之處,則仍然使用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之表述。近年來,針對司法實務中出現的大量非單位犯罪的情況,我國刑法理論界出現了有罪與無罪兩種論調,前者主張按照個人犯罪處理,后者主張按照無罪對待。為了解決實務與理論上的這一爭議問題,我國最高司法機關頒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釋,數量較多且前后立場不一,它們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造成了很多新的問題。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條的解釋》(以下簡稱《單位犯罪立法解釋》),明確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單位實施刑法規定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刑法分則和其他法律未規定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的,對組織、策劃、實施該危害社會行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解釋對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持有罪論的立場。立法解釋出臺后,對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司法實務定罪有據,理論爭議中的有罪論勝出,各方爭議看似頓消。然而,在中國法學界教義學化方興未艾之際,尤其是刑法教義學化興盛發展的大背景之下,以及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九)》)仍堅持單位犯罪法定主義的情況下,立法解釋、司法解釋以及刑法理論對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持有罪論的立場,其實問題重重。對之加以反思,也許正是對我國法教義學事業的尊重。
一、“規范隱退論”與“反教義學化”:一個緊密相關的話題
(一)何為“規范隱退論”?何為“反教義學化”?
晚近以來,隨著中國刑法解釋理論與技藝的日益發達,在一些刑法解釋場合,解釋者看似在解釋刑法規范,實際上卻是在進行“解釋性立法”,以解釋之名行立法之實。在這些場合,解釋的對象即刑法規范看似非常重要,實際作用卻在減弱和隱退。法律成為某些法學研究者手中隨時可以“揉捏”的對象,“創造性成了法律解釋的本質,對法律的忠誠很少被人提及,法律的規范約束作用越來越小”。法律規范的權威受到了質疑,打著各種旗號的刑法解釋例如客觀解釋、實質解釋等被倡導,“法律規范作用的隱退已經在法學研究中實現了‘軟著陸’,成了時髦法學的顯著特征”,法律的“規則之治實際上已經被荒廢”。②法律規范的隱退,意味著創造性法律解釋的凸顯和法解釋對象即法律的規范作用的降低,解釋者的主觀性在法律解釋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法律的權威在降低,這種帶有“規范隱退”性質或傾向的主張可被稱為“規范隱退論”。
刑法教義學的日益發展使刑法理論日益豐富,尤其是刑法解釋論得到了極大發展。然而,此種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加劇了規范隱退的現象,這恐怕是法教義學者始料未及的。如果法學界也有熱搜榜,那么其頭條毫無疑問是法教義學,法教義學是當下中國法學研究者最為熱衷的法學研究范式。法教義學來源于德文Rechtsdogmatik,其中的dogma意指定理、原理或原則,后來引申為教義或信條。因此,教義學就是討論原理、原則或教義、信條的理論學說,是指“信奉特定的思想或經典的思維方式和理論。法律信條論的信奉對象當然就是法律本身,而且包括法律的原理和原則”。③在刑法教義學者看來,刑法教義學等同于刑法解釋學,④其原因在于,“從歷史上看,法律的權威不是建立在人們對它的理性研究的態度之上,而是借助于政治上的強者。因此,傳統法學對法律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種對之深信不疑的基礎上,而鮮有批判精神。一如對圣經的解釋態度,法律解釋學也因此被稱為獨斷型解釋”。⑤這決定了法教義學從一開始就和法解釋學產生了密切的聯系,并進而被我國學者作為將刑法教義學等同于刑法解釋學的理由。由于刑法教義學強調其是對“確切的概念進行理解,從而使正當的判斷成為可能”,⑥簡言之,是對刑法規范的解釋及其基礎上的體系化,這就導致刑法教義學者認為將不好的法律解釋為好的法律,才是一個刑法教義學者的最高追求,由此導致了法治立場的喪失和對法規范的解釋性消解,并在此基礎上延伸出解釋技藝豐富、解釋功能強大,乃至無所不能的“解釋萬能論”,卻忘記了解釋的合法性應該取決于對法規范的恪守而不是超越。由此一來,在一直以來為人所傳誦的刑法格言“法律不是嘲笑的對象”的影響下,刑法教義學者都在基于釋法中心主義而致力于對刑法規范的解釋,并在對法規范的解釋中隨著解釋機能的日益強大而最終使解釋超越了規范,解釋日益成為解釋者個人意志的體現,而不是對法規范的忠誠詮釋;法教義學的解釋功能發展成為準立法功能,刑法學者似乎正在打著法教義學的旗號消解法教義學,我國刑法學的教義學化也因此滑向了“反教義學化”。
刑法解釋學雖然認為“法官解釋法,但不制定法”,⑦然而,解釋者卻在越來越多的場合引導著法官去制定法,解釋者不斷通過新的解釋結論沖破刑法規范的既有邊框,刑法規范的約束功能被合理性、正當性等實質與客觀需求取代。比如,在沒有探討刑法第13條的但書是否適用于類似于醉駕、扒竊等行為的出罪的情況下,就直接將該但書適用于輕微罪予以出罪,從而實際上相當于消解了刑法第133條之一的危險駕駛罪與刑法第264條扒竊型盜竊罪的刑法規范;將過失共同犯罪強硬解釋為刑法第25條的共同犯罪,從而消解了該條“故意共同犯罪”之明確規定;將生產經營的內容擴大解釋為幾乎所有領域和空間的業務,從而消解了刑法第276條破壞生產經營罪的規定;將承諾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解釋為刑法第388條中的“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從而消解了該條的該規定;將幾乎一切沒有被規定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解釋為“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從而消解了刑法第114條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規定;將所有打群架而且不論打了或沒打的行為解釋為聚眾斗毆罪,從而消解了刑法第292條的規定;不加區分將盜竊所有虛擬財產的行為解釋為盜竊罪,從而消解了刑法第264條盜竊罪的規定;將玉米案中的正常買賣行為解釋為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罪,從而消解了刑法第225條的規定;將有償使用搶票軟件的行為解釋為倒賣車票,從而消解了刑法第227條第2款有關倒賣車票、船票罪的規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規范隱退論”與“反教義學化”的一體化關系
“規范隱退論”與“反教義學化”是一體的,規范隱退論就是反教義學化。“規范性以及法的效力乃法教義學的研究對象”,“法教義學是將成文法和法官法聯結起來的紐帶”,⑧因此,法教義學將現行刑法規范奉為“圣經”,不允許隨意批判而提倡恪守刑法規范的解釋,處理刑法規范而非法律事實是刑法教義學的邊界,而在解釋刑法規范時,不允許以刑法規范之外的東西為基礎,正因如此,才會有“法教義學彰顯對法條的尊崇”⑨之論斷。總之,法教義學化以法律規范為核心,以法律解釋為方法,以教義發展與體系構建為理論目的,以服務司法實務為實踐目的。如前所述,法教義學是一種獨斷型解釋。根據康德的觀點,“教義學是‘對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純粹理性的獨斷過程’,教義學常從某些未加檢驗就被當作真實的、先予的前提處罰,法律教義學者不問法究竟是什么,法律認識在何種情況下、在何種范圍內、以何種方式存在”。⑩獨斷型解釋與主觀解釋關系深厚,它意味著對立法者意圖的肯認,主張對法規范采用主觀解釋,通過主觀解釋探尋法規范的立法目的。很顯然,法教義學與形式法治以及主觀解釋一脈相承。“相反,所謂的‘客觀解釋’則是主觀的法官造法。因此,主觀解釋是客觀的;客觀解釋也是主觀的。”(11)主觀解釋“釋有”,客觀解釋“釋無”;主觀解釋追尋的是立法者的法意,客觀解釋表達的是解釋者的立場。前述所有導致刑法規范隱退的解釋案例都是采取的客觀解釋,而且是一種極端的客觀解釋。如果說一般的客觀解釋只是豐富法規范的意義,極端的客觀解釋則是在立法,它使解釋結論遠離既有的法規范,規范不再重要,解釋結論創立的新的規范才是目標,一如盜竊罪中扒竊行為一律入罪的規定被架空,而被以但書為由強行解釋為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扒竊行為才能入罪,從而導致其與盜竊數額較大和次數較多的盜竊行為變成一樣的入罪標準。“在司法過程和法律解釋中,追尋法律的原意似乎已經成了笑柄。人們忘記了,法律的獨斷性是與法律解釋的探究性相聯系的,而只是在以探尋的方式尋找意義。”(12)而現在,解釋者對時代背景、打擊需求、利益衡量等因素的過多考慮,使得刑法規范的意義不是被探尋而是被創立,刑法規范只不過是解釋者的泥塑。假時代的客觀需要之名,各種打擊犯罪的現實需求一再挑戰著法律規范的權威性。如果法教義學離開了規范,那就意味著它可能演變為了社科法學或者政法法學,但肯定不是法教義學。法教義學中的教義通過解釋與發展規范而形成,規范又進一步固化教義的地位和作用。比如刑法中的犯罪構成理論,它正是通過解釋刑法分則中的每一個罪刑規范,解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問題,歷經刑法規范與各種不同案件事實的對接,發展出不同的精妙的解釋理論,如主觀歸責與客觀歸責、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等;與此同時,刑法規范又通過總則與分則對構成要件的規定,進一步維護和發展了犯罪構成理論。離開了規范,法教義學就沒有解釋的對象,進而也無法形成“教義”。當下,中國法學教義學化熱潮涌動,教義學研究成就斐然,然而,很多教義學者打著教義學的幌子,以教義學研究之名在解構規范、消滅教義。當種種刑法解釋看似圍繞刑法規范進行而實際卻是在違背甚至拋棄刑法規范之時,不但表明刑法規范在隱退,而且也是對法教義學的背離和違反,因為這與法教義學以規范為核心的宗旨愈來愈遠。
規范隱退論以及反教義學化的共同危害是損害形式法治。形式法治是法治的阿喀琉斯之踵,突破形式法治就是反法治。法律規范是形式法治的體現,代表了法的安全性、穩定性、可預見性等形式法治的重要價值,
因此,對法律規范的尊崇是對形式法治尊崇的必然結果。法教義學之所以得到更多人的擁簇,恰恰是因其天然的形式法治特性。法學界對于形式法治觀的理解和接受,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各部門法學科各種法教義學主張的出現”,如“刑法學科從刑法哲學、刑事政策學等多元視角回歸到對刑法教義學的強調”,因為“法教義學正是一套約束法律判斷,避免恣意,避免法律外因素對法律判斷的影響,保證形式公正的基本工具”。(13)因此,在中國刑法學者批判傳統蘇俄刑法時,刑法教義學成為取代蘇俄刑法理論的新工具,以化解后者的政治性、隨意性等與法治建設不相協調的基因,為此,晚近二十余年來,我國刑法學研究一直行進在刑法知識的教義學化之路上。既然如此,在進行刑法解釋時,就不能置刑法教義學所要求的形式法治之底線于不顧。“刑法學的核心內容是刑法教義學,其基礎和界限源自刑法規范”。(14)刑法規范被遵守的程度決定著形式法治的實現程度,罪刑法定原則的形式側面也要求嚴格恪守刑法規范,因此,刑法教義學的解釋應當在合法性原則的范圍內進行,嚴格恪守刑法規范才能確保解釋結論的形式合法性。法規范隱退的背后,是對法教義學以規范為核心、以形式法治為底線等特質的違反,“以自由為代價而擴大國家的職權,損害主體權利,通過拓展例外大規模地突破法律原則”,(15)最終導致“形式主義法治所張揚的規范作用在降低”,(16)進而導致形式法治受到損害。如果刑法解釋不是強化刑法規范約束國家權力的作用,而是泛化刑法的作用,使之成為隨需就用的兩可之法,則無窮之端就會產生,這將會大大削弱刑法規范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從而導致刑事法治國的目標難以實現。
只有捍衛法教義學的規范思維,才能建立(刑)法教義學。法教義學的特點是重視規范,以規范為前提,對規范的解釋以及體系構建乃至發展出教義,是整個法教義學的核心工作。規范思維的特點是對錯有無直接明了。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屬于罪刑法定之外的罪、未入刑的罪,因而不是刑法意義上的罪,至多只是犯罪學意義上的罪。沒有規定就不能解釋出有規定。比如,刑法分則沒有規定單位可以成為信用卡詐騙罪的主體,就不能通過懲罰單位的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而在事實上將單位作為該罪的主體。規范思維的優點是最大限度地貫徹形式法治,只考慮是否有規范以及是否有罪,而不會僅僅以處罰的實質正當性例如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造成嚴重后果來決定是否入罪。在入罪的問題上,必須恪守規范正義,否則,罪刑法定原則就會失去它的法治意義。實質的判斷是在既有形式條文的前提之下以及對該條文本身的價值拓展,比如對信用卡詐騙罪中“使用偽造的信用卡”的理解,從偽造本身的含義、其與變造的區分以及刑法分則對偽造與變造犯罪的體系性規定等,決定是否將變造行為解釋為偽造,亦即偽造的實質內涵需要根據社會生活的變化來決定。但是,如果信用卡詐騙罪中沒有規定某種行為如惡意透支為犯罪,無論此種行為的危害性后果如何嚴重,也不能以實質超越形式,以后果代替規范進行入罪。不捍衛法教義學的規范思維是反教義學化的,刑法教義學將無從建立。
二、對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之處理:無罪論抑或有罪論
對于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在當下的立法與司法解釋乃至刑法理論上,基本上是以有罪論為主導。然而,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因何形成?是否伴隨有無罪論的不同意見?有罪論的產生及其與無罪論的爭論,是否屬于規范隱退論所說的范疇?有罪論違反了法教義學嗎?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深入了解關于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入罪抑或出罪的觀點的發展脈絡及其現狀。
(一)單位盜竊:三部司法解釋有罪論立場之確立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的逐步推進,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日益頻繁,相應的,各地出現了很多單位竊電案件并日益突出。由于當時的刑法亦即1979年刑法并沒有規定單位犯罪,是否及如何處理單位竊電案件,便成為困擾各地司法機關的一大問題。為此,1996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關于單位盜竊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1996年單位盜竊解釋》),規定:“單位組織實施盜竊,獲取財產歸單位所有,數額巨大,情節惡劣的,應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責任人員按盜竊罪依法批捕、起訴。”
現行刑法施行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企業的經營行為更加活躍,各地的單位盜竊案件此起彼伏。以單位竊電為代表的單位竊取各種能源的案件不斷涌現,從而使單位實施刑法規定的非單位犯罪如何處理,成為一時之間的新問題。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單位不是盜竊罪的主體,因此不應以盜竊罪被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實務中此類問題過于突出,下級司法機關不知如何應對,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怕于法無據,有違罪刑法定原則;不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又有悖于我國以社會危害性主導的犯罪觀。各地司法機關不斷向最高司法機關請示。2002年8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關于單位有關人員組織實施盜竊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2002年單位盜竊解釋》),規定:“單位有關人員為謀取單位利益組織實施盜竊行為,情節嚴重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以盜竊罪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該解釋延續了《1996年單位盜竊解釋》的立場和內容,肯定了對單位實施的盜竊行為應予刑事處罰。在現行刑法第264條盜竊罪沒有規定單位犯罪的前提下,該解釋等于承認了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如盜竊罪)應該以犯罪論處,只不過追究自然人而不是單位的刑事責任,此立場,姑且稱之為單位盜竊的有罪論。
十余年后,盜竊罪無論數額還是表現形式均發生了諸多變化,比如,就單位盜竊而言,發生了很多單位出面組織策劃、指使盜竊犯罪,但又不一定為了本單位利益,可能是為了別的單位利益,可能是為了組織者等的利益的案件,對何為“單位有關人員”也爭議頗多。《2002年單位盜竊解釋》漸漸不能適應盜竊犯罪的變化。為此,2013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兩高”)聯合頒布了《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3年單位盜竊解釋》),其第13條規定,“單位組織、指使盜竊,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及本解釋有關規定的,以盜竊罪追究組織者、指使者、直接實施者的刑事責任”。較之于《2002年單位盜竊解釋》要求“單位有關人員為謀取單位利益組織實施盜竊行為”的規定,該解釋進一步明確和強化了單位盜竊的有罪論立場及追究刑事責任的條件:第一,將“單位有關人員”明確為“組織者、指使者、直接實施者”;第二,將“為謀取單位利益”的規定取消,從而使得沒有為單位謀利的情況也可以被追究刑事責任,擴大了追究單位實施盜竊犯罪的刑事責任范圍。但是,無論如何變化,《2013年單位盜竊解釋》總體上只是借鑒了《2002年單位盜竊解釋》的“相關規定,明確單位組織、指使盜竊,符合刑法第264條及本解釋有關規定的。以盜竊罪追究組織者、指使者、直接實施者的刑事責任”。(17)
(二)單位實施其他非單位犯罪:有罪論的延續與無罪論的出場
晚近二十年,我國其他有關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的司法解釋有四部,其中三部延續了單位盜竊司法解釋的有罪論立場,一部體現了無罪論立場。有罪論與無罪論在司法解釋立場上的對立延續,折射出對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不能武斷地以有罪論一以定之。
體現有罪論立場的三部司法解釋分別是針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計算機犯罪,偷越國邊境犯罪而頒布的。第一部是1998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1998年判決裁定解釋》),其第4條規定,“負有執行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義務的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為了本單位的利益實施本解釋第三條所列行為之一,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對該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規定,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定罪處罰”。刑法第313條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本為只能由自然人構成的犯罪,對于單位實施本罪如何處理,該司法解釋采取了有罪論立場,但只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責任。第二部是2011年8月1日“兩高”頒布的《關于辦理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1年單位計算機犯罪解釋》),其第8條規定,“以單位名義或者單位形式實施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犯罪,達到本解釋規定的定罪量刑標準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在《刑法修正案(九)》頒布以前,刑法第285條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的程序、工具罪,第286條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共四個計算機犯罪罪名均為自然人犯罪,單位本不構成犯罪主體。針對實踐中諸多單位實施計算機犯罪的情況,《2011年單位計算機犯罪解釋》采取了有罪論立場,但不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只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責任。第三部是2012年12月12日“兩高”頒布的《關于辦理妨害國(邊)境管理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2年偷越國邊境解釋》),其第7條規定,“以單位名義或者單位形式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為他人提供偽造、變造的出入境證件或者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條、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十一條的規定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刑法第318條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第320條提供偽造、變造的出入境證件罪,出售出入境證件罪,第321條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罪均為自然人犯罪。該解釋采取有罪論立場,將單位實施上述三種犯罪認定為有罪,并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責任。
體現無罪論立場的一部司法解釋是針對單位實施貸款詐騙罪頒布的。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2001年金融會議紀要》),就單位實施貸款詐騙行為如何處理作出了明確規定:“根據刑法第三十條和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定,單位不構成貸款詐騙罪。對于單位實施的貸款詐騙行為,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也不能以貸款詐騙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單位十分明顯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簽訂、履行借款合同詐騙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刑法第193條貸款詐騙罪是只能由自然人實施的犯罪,當單位實施貸款詐騙行為時,既不能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也不能追究直接負責的自然人的刑事責任。雖然紀要規定有些時候的貸款詐騙行為可以按照合同詐騙罪來處理,但那是因為貸款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存在法條競合關系,而合同詐騙罪屬于既可由單位構成又可由自然人構成的犯罪,當單位實施貸款詐騙行為且符合合同詐騙罪的規定時,按照合同詐騙罪定罪純屬根據法條競合理論處理的結果,即使紀要不如此規定,在理論和實踐中也應如此認識和操作。換言之,紀要關于單位實施貸款詐騙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時按合同詐騙罪處理的規定,屬于重申和提示性的注意規定。因此,《2001年金融會議紀要》對單位實施貸款詐騙罪這種非單位犯罪采取了無罪論的立場,單位實施貸款詐騙行為時,單位和自然人都不能被追究刑事責任。
(三)有罪論對無罪論的終結: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的立法解釋
分析上述七部有關單位犯罪的司法解釋的效力。首先,《1996年單位盜竊解釋》已經失效。2002年2月25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廢止部分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的決定》(高檢發釋字[2002]2號)明確規定廢止高檢發研字[1996]1號,
因此該解釋已失效。其次,根據新法優于舊法原則,針對同一問題的司法解釋只應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原有的司法解釋自動失效。據此,《2002年單位盜竊解釋》失效,應該適用《2013年單位盜竊解釋》。因此,上述七部司法解釋仍然有效的應該是《1998年判決裁定解釋》、《2011年單位計算機犯罪解釋》、《2001年金融會議紀要》、《2012年偷越國邊境解釋》、《2013年單位盜竊解釋》。去掉兩部失效的司法解釋,剩下的五部司法解釋仍完整地體現了關于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的有罪論與無罪論的對立。
為解決以上司法解釋的相互矛盾,防止今后再出現單位實施其他非單位犯罪無法可依的情況。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了《單位犯罪立法解釋》,明確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單位實施刑法規定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刑法分則和其他法律未規定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的,對組織、策劃、實施該危害社會行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較之有關單位犯罪的司法解釋,該立法解釋無疑具有普遍適用性。《單位犯罪立法解釋》沿襲了以關于單位盜竊犯罪的系列司法解釋為代表確立的有罪論立場,統一明確規定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時一律按照犯罪處理,并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責任;同時,該立法解釋將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視為自然人犯罪的傾向非常明顯。《單位犯罪立法解釋》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之前有關單位犯罪的司法解釋之間立場矛盾的問題,并宣告了《2001年金融會議紀要》無罪論立場的終結,使得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認定統一化、清晰化。
從1996年有關單位犯罪的第一個司法解釋到2014年有關單位盜竊的立法解釋,在近二十年的時間中,對單位實施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的處理,從有限的有罪論(僅限于盜竊罪)到無罪論,再到全面的有罪論的確立,從而使得刑法第30條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節節敗退并最終隱退,法教義學對法規范的背離以此為例,無有出其右者。
三、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對形式法治的消解:導致“規范隱退”與“反教義學化”
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的全面勝利,恰恰意味著刑法規范的隱退與法教義學志業的受損。從根本上看,有罪論是反規范主義與反教義學化的,它從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出發,以處罰的合理性和打擊單位犯罪的現實需要消解刑法規范乃至形式法治的意義,對此,既需警惕,更需深思。
(一)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對形式法治的消解之一:導致“規范隱退”
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是迄今為止刑法領域“規范隱退論”的最典型代表。有罪論關注的是社會效果而不是法律效果,是“端著法律的飯碗瓦解法律”(18)的行為,其置刑法第30條的規定于不顧,慨然通過對刑法的學理解釋、司法解釋乃至最終立法解釋,于實質上創設了新的單位犯罪的規定,刑法第30條的規定以及刑法第3條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全部隱退乃至被消解。
在現行刑法頒布之前,1979年刑法既沒有規定單位可以成為犯罪主體,也沒有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為了打擊單位盜竊,《1996年單位盜竊解釋》將單位盜竊按照自然人盜竊對待并處理的做法是可行的。事實上,早在1985年7月18日“兩高”頒布的《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答》中就已有了類似規定。該解答第4條明確規定:“國營單位或集體經濟組織,不具備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其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以騙取財物為目的,采取欺詐手段同其他單位或個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數額較大,給對方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的,應按詐騙罪追究其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如果經對方索取,已將所騙財物歸還的,可以從寬處理。”沒有單位犯罪的刑法規定,意味著對上述單位犯罪案件按照自然人處理是合適的;也正因為現實中不斷發生上述單位犯罪案件,同時當時的刑法理論和實踐均認為對其“只按照自然人犯罪處理”不合適,(19)那樣無異于放縱了單位的責任,所以刑法理論界和實務界才推動現行刑法增加了單位犯罪的規定。換言之,在單位犯罪的前法定主義時代,上述做法只是權宜之計。
1997年刑法增加了單位犯罪的規定。刑法第30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據此,在我國刑法中,對單位犯罪采取的是法定主義,亦即只有在刑法分則的相關罪名中明確規定單位為其犯罪主體的犯罪才是單位犯罪。比如,刑法第198條保險詐騙罪是單位犯罪,因為該條第3款明確規定,“單位犯第一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現行刑法第264條盜竊罪并沒有規定單位可以構成本罪,換言之,盜竊罪只能由自然人構成,它不是單位犯罪。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刑法第3條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在現行刑法單位犯罪的法定主義以及罪刑法定原則法典化的背景之下,《2002年單位盜竊解釋》與《2013年單位盜竊解釋》延續《1996年單位盜竊解釋》有罪論的立場令人質疑。同時,通過另外三部關于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的司法解釋,即《1998年判決裁定解釋》、《2011年單位計算機犯罪解釋》與《2012年偷越國邊境解釋》,有罪論從單位盜竊犯罪蔓延到單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單位計算機犯罪,單位偷越國邊境罪。這種趨勢使得我國刑法對于單位犯罪的處罰范圍日益擴大,那些原本只能由自然人構成的犯罪,通過這六部司法解釋,在實際上也變成了可以由單位構成的犯罪,只不過采取的是只處罰自然人的單罰制。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的有罪論立場,無疑是面對現實中大量發生的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的現象,為了發揮刑法打擊犯罪、治理社會的功效,在單位犯罪的法定主義之外,采取的一種實用主義、便宜主義的立場。縱然《2001年金融會議紀要》持無罪論的立場,然而,該解釋只能在個罪中適用,難以與有罪論抗衡。《單位犯罪立法解釋》頒布之后,根據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基本法理,以往有效的五部司法解釋應該不再使用,而直接使用該立法解釋。《單位犯罪立法解釋》的頒布,使得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一律有罪化,導致刑法的處罰范圍急劇擴張;對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的處罰不再只適用于個別犯罪,而是適用于所有犯罪。刑法實務處理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不再糾結于“法律是否規定為單位犯罪”,刑法有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按照刑法條款處理,采用雙罰制追究單位刑事責任;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按照立法解釋處理,采用單罰制追究個人刑事責任。面對所有的單位犯罪,刑法實現了一網打盡的社會治理目標;刑法第30條成為擺設,其規范意義與效果被徹底架空,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刑法第30條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的一再隱退。一個法治國家應該堅持規則功利主義,規則至上意味著法治主義,離開規則主義不可能實現法治。規范隱退的后果是對刑法權威性的破壞,是對形式法治的突破。在此,我們看不到規范,只看到現實;看不到罪刑法定,只看到出入人罪;我國刑法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罪刑法定原則乃至刑事法治事業均受到嚴峻沖擊。
(二)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對形式法治的消解之二:導致“反教義學化”
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是晚近中國刑法教義學化過程中最明顯的“反教義學化”。有罪論不是以刑法規范為核心,不是通過對刑法規范的邏輯分析并將之上升為體系的教義化過程來解決打擊單位犯罪的現實需求,而是粗暴地通過有權解釋修改了原有的刑法規范,破壞了法教義學的安定性價值。有罪論使用的不是刑法教義學這一工具,但它卻又確確實實為刑法教義學者所贊同,它是打著法教義學的名義通過解釋刑法規范瓦解刑法規范,最終乃是打著法教義學的名義瓦解法教義學。
法學為什么會走上教義學之路?對這一問題需要反思。面對基爾希曼提出“作為科學的法學的無價值性”這一命題,耶林以“法學是一門科學嗎”加以回應,拉倫茨則以“論作為科學的法學的不可或缺性”加以回應,這些均表明,法教義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拯救法學自身,是為了讓法學更加接近科學乃至最終成為一門科學而進行的一種技術上的努力。傳統的法教義學極其強調形式主義與邏輯體系的價值取向,現代的法教義學在自由法運動的推動下雖然呈現開放性,但其基底從未改變,那就是“通過一種概念形式主義的教義學給法律帶來可計算、可預測的理性主義”,(20)通過對規范的解釋和體系化構建推動法教義的形成,使得規范與正義高度統一,因此,法教義學具有落實和強化法的安定性價值之功效。
然而,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恰恰是對規則主義、形式主義的破壞。在現行刑法施行之后,單位犯罪的法定主義只維持了短短的一年時間。隨著《1998年判決裁定解釋》等一系列關于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的司法解釋與立法解釋的頒布,單位犯罪的法定主義屢受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沖擊。在現行刑法既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又實行了單位犯罪的法定主義的背景下,將現行刑法施行之前應對單位犯罪只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責任的權宜之計,推廣到所有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的情況,無疑是對罪刑法定原則和單位犯罪的法定主義的嘲諷。“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是否應追究刑事責任”的本質問題,是一個如何看待罪刑法定主義,如何看待單位犯罪的法定主義與功利主義之間的關系,如何在處理單位犯罪中貫徹責任主義等的基本問題。
罪刑法定是刑法規則主義、形式主義、理性主義的制擎和總體現。當今世界各國,“無論是對法人犯罪持肯定態度還是否定態度的國家,對法人活動的刑法規制問題上,均是抱著一種非常矛盾的心情,在必須以刑法手段對犯罪學上所謂的法人犯罪進行規制的功利考慮和如何堅持近代刑法基本原則之一的責任原則之間踟躕徘徊”。(21)在單位犯罪問題上,我國的司法解釋與立法解釋有罪論與無罪論的對立,恰恰體現了這一點。《單位犯罪立法解釋》雖然從刑法解釋的效力上以有罪論終結了無罪論,但在刑法理論的探討上,這一問題遠未完結。在《單位犯罪立法解釋》頒布之后,如何看待關于單位實施盜竊罪這種非單位犯罪的有罪論與《2001年金融會議紀要》所確立的關于單位實施貸款詐騙罪這種非單位犯罪的無罪論之間的立場對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對如何看待《2001年金融會議紀要》的無罪論與另外六部司法解釋的有罪論之間的立場對立問題的回答。簡單地以立法解釋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釋的效力而將此問題完全回避掉,恐怕對于推動關于單位犯罪的立法、理論與實踐毫無助益。即使以立法解釋之效力強行推行有罪論,也無法正面回答為何對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予以處理這一涉及罪刑法定原則的根本性問題,由此一來,直接動搖了刑法教義學的安定性價值。
“如果有人基于政治的、倫理的或者社會效果的因素試圖背離既有的教義學規則,則必須承擔相應的論證負擔。”(22)為此,不妨看看有罪論是如何論證的。無罪論認為,在單位盜竊案件中,盜竊行為具有單位屬性,不能認定為自然人的行為,且單位盜竊的受益主體是單位而不是自然人,對此種行為應以單位犯罪論處。但是,由于單位不是盜竊罪的主體,故單位不構成犯罪,更不能以盜竊罪為名將單位盜竊行為轉嫁到自然人身上并追究刑事責任。(23)有罪論主張,單位實施非單位犯罪,意味著是自然人在實施犯罪,因此,如果不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那也應該追究自然人如直接責任人員等的刑事責任。(24)持該種觀點的學者認為,無罪論如果成立,導致的后果將不堪設想。(25)比如,甲科技創新公司為了在與乙科技創新公司的競爭中保持優勢,決定殺掉乙科技創新公司的某著名海外科學家。甲科技創新公司經董事會密謀后,出巨資派出了公司中略會武功的某保安丁殺害了該著名海外科學家。本案中,甲科技創新公司及其負責人、保安丁是否成立故意殺人罪?有罪論的論證“將問題抵在了槍口上”,非常尖銳。但是,有罪論的論證并非不可反駁。
對殺人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顯然違反一般國民的法情感。不管是在“德國等少數不承認法人犯罪的歐洲大陸國家的刑法中”,還是在“承認法人犯罪的英美法系國家的刑法中”,“不存在法人雇員實施純正自然人犯罪不受懲罰的問題。法人雇員只要實施犯罪就必須承擔刑事責任”。(26)這在刑法理論和司法實務中并不存在任何爭議。換言之,單位集體決定而派職工實施的殺人行為,在刑法技術上被處理為自然人犯罪沒有任何困難,因為殺人罪屬于極端犯罪,個人即可實施。單位集體決定而派職工實施的殺人行為類似于個人被勸喝酒后開車肇事的原因自由行為,職工可以選擇殺或不殺,這和單位盜竊等財產經濟犯罪根本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類似于故意殺人罪、搶劫罪、強奸罪等犯罪行為,即或是由單位決定派職工實施,但這類人身犯罪屬于身份行為,即只能由個人親自實施的犯罪行為,個人在實施過程中,完全能夠意識到這類行為的性質與意義,在此情況下仍然實施的,無論單位是否構成犯罪,根據犯罪構成理論,對實施這些行為的個人追究刑事責任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人身犯罪單位無法直接實施,必須經由個人之手;財產經濟犯罪單位可以直接實施而且效果可能更好。如果說對單位犯罪之所以處罰單位的責任人員是因為對于單位整體而言如刑法學家考菲所說“沒有可譴責的靈魂,沒有可處罰的身軀”,那么,在單位派職工實施殺人罪的情況下,職工自身既有可譴責的靈魂,又有可處罰的身軀,此時,將職工個人的殺人行為作為純粹的自然人犯罪加以處罰,完全符合罪責自負的刑事歸責原理。這意味著,無論是否有司法解釋或立法解釋,對以單位名義實施的這些人身犯罪行為不需要討論是否處罰的問題,否則就是強不同以為同,并將刑法第30條的“規范正義”與刑法第232條的“個案正義”相混同,這樣的論證本身就不夠教義學化,以之為理由主張對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一律入罪,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既然如此,有罪論的恣意性以及對統一法律規范的破壞性,對罪刑法定原則這一形式法治底線的逾越,都將成為其難以擺脫的指責。“從形式的角度看,刑法主要是保證法安定性的法治國家原則的要素。由于刑法可能對公民的個人自由予以最嚴厲的干涉,因此尤其需要采取特殊的預防其被濫用的措施。”(27)在面對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時,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不應沖破規則主義的藩籬,不應濫用刑法處罰。離開規則約束的功利主義充滿了社會本位的刑罰擴張思想,“功利主義的解釋思路往往會努力擺脫法律的束縛,突破基本的人權邊界,尤其是在保護法益、保護社會的絕對‘政治正確’的名義下,更容易將解釋進行到底而‘榨干’法條,使得人們喪失對刑法可能成為‘惡’的必要提防與警覺意識”。(28)有罪論使得所有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都可以被追究刑事責任,導致刑法第30條的規定不但被榨干而且被架空,從而使對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的處罰不受形式法治的價值約束,單位犯罪的法定主義變成普遍主義。在這里,不是法律規范優先,不是法治邏輯優先,而是生活價值優先,治理犯罪的現實需要優先。法教義學所倡導的法律解釋方法要求“表達精確傳遞的規則”(29)而不是解釋性的立法,有罪論恰恰是破壞形式法治的解釋性立法。
符合法規范與解釋規則的結論才具有刑法教義學上的解釋力。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欠缺刑法教義學意義上的解釋力。刑法第30條與刑法分則規定單位犯罪的法條之間是一脈相承的關系,后者是前者的體現,前者是后者的約束,它們之間相互形成一個協調的法律體系,但有罪論打破了這種體系協調性。“如果某個理論最大程度的符合了解釋規則和人們的基本范式,那么,這個理論就擁有了最大的解釋力”。“如果教義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價值矛盾、顯然違背了詞義、忽視了體系性聯系,或者得出了公然不顧規范之目的的結論,那么,我們就可以較容易地判定,這種教義學理論是站不住腳的。”(30)因此,如果理論與現行法規范之間相互沖突,那么,理論的解釋力就會減弱甚至消失。片段性的法益保護體系是刑法教義學的體系性工作之限制與特征。有罪論是對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這一問題的局部解釋,而不是基于刑法典與法治原則的整體解釋。這種解釋方式“把刑法機制當成社會現實的一個機能性要素來把握”,(31)而不是把刑法機制當成有關刑罰介入正當化的根基性問題來反思。在后者,刑法教義學是用來控制處罰范圍邊界的。刑法具有片段性和不完整性,它不可能保護社會生活中的所有法益,而只能打擊應受刑法處罰的侵害法益的行為,保護那些重要的法益。這種選擇性的法益保護恰恰是從犯罪論體系上對刑法的限制。為了懲罰單位犯罪,刑法通過設立“禁止規范來保障一個預先確定的法秩序”。(32)例如,為了懲處單位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等單位金融詐騙罪,通過刑法第194條、第195條以及第200條共同達到這一目的。如果發現了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如單位集資詐騙罪、單位貸款詐騙罪、單位信用卡詐騙罪等,就不處罰。換言之,作為法律體系最后手段與屏障的刑法,其不完整性已經得到人們的普遍接受。而且,“刑法本來是被限制在保護個人化的法益以免受侵害這樣的任務上的,人們也將這種刑法稱為服務于法治國家這一導向的刑法,可是,目前刑法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偏離這種‘法治國家導向’了”。(33)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不是為了保護個人化的法益免受侵害,而是為了社會化、集體化的法益免受侵害,它不是服務于法治國家的導向,而是服務于福利國家的目的;它不是與刑法規范體系相協調的解釋,而是基于預防犯罪、懲罰犯罪的刑事政策需要而產生。有罪論違反了刑法教義學化的趨勢與要求,是中國刑法偏離法治國家導向的明顯體現。有罪論事實上是以實質解釋突破刑法的形式規定,以利益考量沖破刑法規范,對于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如貸款詐騙罪等以單位犯罪論處,是基于此類行為嚴重侵害法益的實質利益考慮,擔心不追究就會放縱犯罪,從而廣泛地“將利益均衡(Gueterabwaegung)原則引進民、刑法之解釋適用中”。(34)尤其是以法益保護為目的的刑法,基于利益衡量原則解釋適用刑法規范當屬其常用之解釋方法。然而,此種解釋方法僅適用于法律有規定之時,亦即是對現行法的解釋,而不應對法無明文規定的“犯罪”進行入罪解釋。如果僅因某行為的法益侵害性嚴重就將其入罪,則意味著利益衡量超越了刑法規范的適用根據。此種做法是對刑法規范的消解,也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消解,對法治主義的消解。法益是刑法教義學的核心概念和重要教義。使用它應該是為了法教義學的形式法治基本目標的實現,而不是擴大法益的內涵和外延,增加入罪的隨意性和可操作性,以法教義學的名義瓦解法教義學。
(三)形式法治的重申:以《刑法修正案(九)》關于單位犯罪的立法為例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刑法修正案(九)》對于其所認為的單位犯罪,仍然采取的是“單位犯……罪的,處……刑”的法定主義,而并未適用全面有罪論的《單位犯罪立法解釋》。這意味著,《單位犯罪立法解釋》并沒有從根本上撼動單位犯罪的法定主義,形式法治通過《刑法修正案(九)》關于單位犯罪的立法得到了堅守。
這恰恰給了刑法學理反省的機會: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可能存在疑問。根據有罪論,既然所有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都可以按照《單位犯罪立法解釋》追究刑事責任,那么,為何《刑法修正案(九)》對單位犯罪仍然采取法定主義?對于單位犯罪,《刑法修正案(九)》仍然根據刑法第30條采用了“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才“應當負刑事責任”的立法形式,這無疑令人深思。比如,《刑法修正案(九)》將刑法第313條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由自然人犯罪規定為單位犯罪,其第39條規定:“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再如,在《刑法修正案(九)》頒布之前,刑法第285條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的程序、工具罪,第286條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這四個罪都是自然人犯罪,單位不構成犯罪主體。為此,2011年8月1日“兩高”頒布的《關于辦理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規定:“以單位名義或者單位形式實施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犯罪,達到本解釋規定的定罪量刑標準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這一司法解釋無疑完全可以解決這幾個計算機單位犯罪的處理問題,一如前述幾部有罪論的司法解釋一樣,更何況還有《單位犯罪立法解釋》,根據立法解釋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釋的效力的基本法理,也完全可以直接適用立法解釋。但是,《刑法修正案(九)》第26條、第27條分別修改了刑法第285條、第286條,增加了單位犯罪主體。其第26條規定:“單位犯前三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各該款的規定處罰。”其第27條規定:“單位犯前三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總之,《刑法修正案(九)》以11個條文對12個罪名增加規定了單位犯罪,大大擴展了我國刑法單位犯罪成立的范圍。
毫無疑問,對于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并沒有因《單位犯罪立法解釋》已經解決了問題而置之不管,反而置該立法解釋于不顧,再度回歸刑法第30條單位犯罪的法定主義。它明確表明,除了前述11個條文規定的12個罪名單位可以成為犯罪主體之外,另外沒有特別規定“單位犯前款罪”的,一律不能認定為單位犯罪。否則,這11個條文對單位犯罪主體的規定就多此一舉。這似乎意味著,持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的司法解釋和立法解釋,其實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并不代表對刑法理論上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的肯認;或許這還意味著對《單位犯罪立法解釋》隱退刑法規范、違反法教義學以及破壞形式法治的某種糾正。即便以上揣測都不準確,至少它也表明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并不穩妥,將有罪論推廣適用于所有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既不符合立法本意,也不符合立法現實。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對單位犯罪法定主義的回歸,恰恰表明了有罪論可能欠缺規范上的合法性與學理上的正當性,對之應該持謹慎與反省的態度,而不是推而廣之的態度。同時,《刑法修正案(九)》對單位犯罪法定主義的堅守也表明,未來我國刑法單位犯罪的立法與司法解釋如何統一、如何走向,顯然還是一個未完待決的問題。
對于刑法而言,保護所有受侵害的法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刑法保護的不完整性通過罪刑法定原則得以固守,通過刑法規范予以載明,通過刑法教義學得以實現。法無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有罪論無視刑法第30條以及刑法分則對單位犯罪的明文規定,通過對單位有關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的處罰,變相地將單位犯罪擴大于所有犯罪,導致刑法中的全部犯罪實際上都可以由單位構成。對于刑法的科學解釋應該圍繞刑法規范進行,但是,有罪論讓人看不到刑法規范,規范被隱退在解釋者的解釋結論之后;看不到規則主義,只有打擊犯罪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在蔓延。有罪論是一種新的責任轉嫁,它強化了個人責任以彌補企業自身的不足,不利于現代企業制度的構建;有罪論也模糊了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之間的界限。在刑法理論上,中國刑法采用了大陸法系“法人實在論”的觀點,并進而在刑事立法上承認單位可以成為犯罪主體,以“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的立法模式確立了追究單位刑事責任的刑法規范依據,從而使“法律沒有規定單位犯罪則不應當負刑事責任”成為必然的結論。中國刑法如果要實行教義學化必須恪守規范主義。法教義學的研究取向是以現實生活事件的規范問題為核心,因此,法教義學首先應關注的是現行的法律制度,例如罪刑法定主義等各種既存制度,其次才是兼顧社會普遍承認的各種價值。這意味著,形式正義與形式法治是法教義學的前提,在單位犯罪等具體問題的研究中,絕不能罔顧刑法規范,拋卻形式主義的教義如罪刑法定原則等,一味遷就于功利主義、實用主義。
注釋:
①Cohn/Wendland,Philonis Opera,Band3,1926,S.66.轉引自周升乾:《法教義學研究—— 一個歷史與方法的視角》,中國政法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2頁。
②陳金釗:《法律人思維中的規范隱退》,《中國法學》2012年第1期,第5頁。
③陳妙芬:《Rechtsdogmatik——法律解釋學,還是法律信條論?》,《月旦法學雜志》2000年第3期,第183頁。
④參見張明楷:《也論刑法教義學的立場》,《中外法學》2014年第2期,第362頁;陳興良:《刑法教義學彰顯對法條的尊崇》,《檢察日報》2014年7月31日,第3版。
⑤焦寶乾:《法教義學的觀念及其演變》,《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第89頁。
⑥[德]沃爾福岡·弗里希:《法教義學對刑法發展的意義》,趙書鴻譯,《比較法研究》2012年第1期,第143頁。
⑦張明楷:《刑法格言的展開》(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頁。
⑧[德]維滕貝爾格:《德國視角下的基礎研究與教義學》,查云飛、張小丹譯,載李昊、明輝主編:《北航法律評論》2015年第1輯,第5頁。
⑨同注④,陳興良文。
⑩[德]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主編:《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11)K.F.Rhl,Allgemeine Rechtslehre,Kln 1995,S.649.轉引自[德]魏德士:《法理學》,丁曉春、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346頁。
(12)同注②,第10頁。
(13)張翔:《形式法治與法教義學》,《法學研究》2012年第6期,第8頁。
(14)[德]耶賽克、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上),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頁。
(15)[德]卡爾·恩吉施:《法律思維導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頁。
(16)同注②。
(17)陳國慶、韓耀元、宋丹:《解讀“兩高”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司法解釋》,《檢察日報》2013年6月5日,第3版。
(18)同注②,第6頁。
(19)參見黎宏:《近年來國外法人刑事責任理論的若干特點》,《比較法研究》2002年第4期,第37頁。
(20)陳輝:《德國法教義學的結構與演變》,《環球法律評論》2017年第1期,第157頁。
(21)同注(19),第36頁。
(22)同注(13)。
(23)參見陳興良:《盜竊罪研究》,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判解》(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頁。
(24)參見張明楷:《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頁。
(25)參見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374頁。
(26)王良順:《論參與實施純正自然人犯罪的單位成員的刑事責任》,《法商研究》2013年第2期,第93頁。
(27)同注(14),第36頁。
(28)蔡道通:《特別法條優于普通法條適用——以金融詐騙罪行為類型的意義為分析視角》,《法學家》2015年第5期,第38頁。
(29)同注⑩,第272頁。
(30)[德]金德豪伊澤爾:《適應與自主之間的德國刑法教義學》,蔡桂生譯,《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第148頁。
(31)同注(30),第149頁。
(32)同注(14),第77頁。
(33)同注(14),第77頁。
(34)王立達:《法釋義學研究取向初探:一個方法論的反省》,《法令月刊》2000年第9期,第28頁。
版權聲明:本文內容由互聯網用戶自發貢獻,本站不擁有所有權,不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如果發現本站有涉嫌抄襲的內容,歡迎發送郵件至 [email protected]舉報,并提供相關證據,一經查實,本站將立刻刪除涉嫌侵權內容。
標簽:
相關文章
武當山旅游門票是通往武當山探訪的必備“通行證”。想必許多人都曾懷著探尋武當山的美麗與奧秘的向往,而購買門票,便是實現這一向往的第一步。武當山旅游門票如何購買?或許這個問題曾讓你迷茫,但通過這篇文章的……
2024-07-11
天露山旅游度假區位于中國禪都-廣東省云浮市新興縣,天露山是粵中南部高峰,海拔1251米。山上終年云霧繚繞、奇石遍布、山花爛漫,杜鵑花、梅花、禾雀花、石榴花、山茶花、桫欏以及各種珍稀花木等組成了一座綠色……
2024-06-29
清明京郊自駕游:踏青賞春樂悠悠 清明京郊自駕游去哪兒好玩? 北京周邊廣袤無垠,歷史遺跡與自然風光交相輝映,清明小長假自駕出行正當其時。推薦以下京郊自駕游好去處: 1. 慕田峪長城:雄偉壯觀的長城,賞春登……
2024-06-01
深圳大華興寺四面山水簇擁,風景優美建筑多為仿唐風格,是佛教寺廟,隱藏在鬧市中的一片安詳地,在國慶節過來游玩需要預約嗎,大華興寺觀音懺法會是什么時候? 深圳大華興寺介紹 大華興寺位于深圳東部華僑城的“觀……
2024-06-21
旅游簽新加坡去印尼所需時間因具體情況而異。一般而言,新加坡公民或持有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士可以免簽證前往印尼旅游,停留期限為30天。以下為您解答更多相關問題。 在新加坡如何申請去印尼的旅游簽證 新加……
2024-07-09
老撾和泰國是東南亞國家,對于中國公民來說,落地簽入境是一種相對方便的方式。本文將從簽證申請、入境要求、停留期限和出入境信息等多個方面對老撾和泰國的落地簽入境要求進行闡述。 1、簽證申請 2、入境要求 3……
2024-10-31

最新資訊
2024蘇州濱河路地鐵口櫻花最佳觀賞期 蘇州濱河路地鐵站
重慶江津貢桃花源門票多少錢 江津桃花山莊電話
2024第十屆廣州易行車展免費門票在哪里領?
2024蘇州濱河路地鐵站櫻花開了嗎,蘇州地鐵一號線濱河路出口
沈陽新世界博物館在哪里,沈陽新世界博覽館營業時間
李家峽旅游攻略一日游 李家峽景區門票多少錢
國內著名旅游景點介紹 國內著名旅游景點介紹作文
2024年清明節是幾月幾日星期幾 2024年清明節是幾月幾日星期幾呢
2024年3月廣州車展匯總 三月廣州車展
甘南郎木寺旅游攻略 甘南郎木寺景區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