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增定:從“中國哲學”的學科焦慮意識談中國學術的文化自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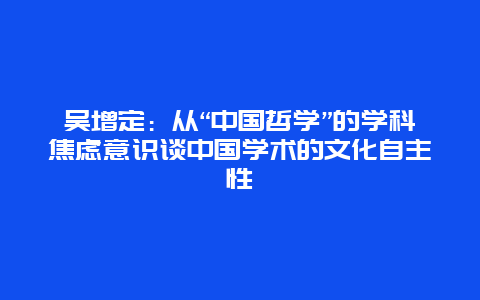
近年來,中國哲學的研究不管是在一般的思想史和觀念史層面,還是在實證性的考古層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這種進步給“中國哲學”這門學科所帶來的卻不是自信,而是一種深刻的焦慮感。隨著我們對中國思想越來越深入的了解,我們就越發感到困惑:與西方自柏拉圖以來的兩千多年主流哲學傳統相比,我們既沒有嚴格意義的本體論、宇宙論、認識論,也沒有嚴密的邏輯分析方法和哲學體系,既然如此,那么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思想傳統還能否被叫做“哲學”?倘若是哲學的話,那么又在什么意義叫做“哲學”?自上個世紀初以來,中國學者一直為此問題所困擾,今天這種困擾非但沒有消除,甚至更加強化了。譬如說,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居然成為2003年國內十大熱門學術話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其實,中國學者的這種困惑和焦慮感,無非是出于一個非產簡單的原因:中國并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哲學”。中文的“哲學”一詞,本是取自日本人西周的創造,此人在《百一新論》中首先用“哲學”翻譯英文的philosophy。在這之后,中國人才用“哲學”來概括中國自己的傳統思想。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看似是對“中國哲學史”的客觀實證研究,但實質卻不過是證明:中國思想根本就沒有西方意義的嚴格哲學精神。在新文化運動之后,以馮友蘭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為標志,中國學者開始自覺地建構中國人自己的“哲學”和“哲學史”。隨著“中國哲學”被北大和清華等現代大學納入學科編制,“中國哲學”在文化和制度兩個方面都取得了相當程度的“自主性”。
但是,“中國哲學”之學科“自主性”的建立并沒有平息中國學者的焦慮和爭論,因為他們看到,“中國哲學”不管是在前提還是在論述方式上都是以西方哲學為模型:既然西方哲學有本體論、形而上學和認識論等,我們就要相應地建構類似的哲學門類;既然西方有邏輯分析方法,我們就要在中國思想中尋找體系。但是,說到底,“中國哲學”的建構不過是對西方哲學的一種仿造而已,至于中國自己有沒有“哲學”仍然頗成問題。況且,用西方的哲學概念、范疇和體系來解釋中國思想,難免讓人有削足適履之感,更不用說,這其實是對中國思想內在整體和脈絡的根本扭曲和肢解。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哲學”就是在不斷的批判與建構、懷疑與自信、焦慮和振奮之中曲折前行。
稍稍追溯“中國哲學”的發展歷史,就不難發現:“中國哲學”一百多年的學科建構歷史,恰恰跟中國一百多年的救亡圖存歷史密切相關。近世以來,在西方帝國主義船堅炮利的侵略下,中國人為避免亡國滅種的命運,被迫不斷反省自己的傳統,從最初的“器物”變革,到后來的“制度”變革,一直到最后的“文化”變革,中國人最終將落后的原因歸結為自己的“文化”傳統。當時的中國士大夫和知識階層認為:與西方相比,我們沒有自由平等民主個人主義科學資本主義……既然所有這些因素都是哲學精神的體現,那么說到底,我們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是因為我們沒有哲學!。
因此,就哲學而言,要想真正地確立中國的文化自主性,我們首先應該理性地檢討過去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現代性歷史。在整個二十世紀,出于“救亡圖存”的焦慮,我們將建立現代國家作為自己的根本使命,一切學術和文化的建樹無不服從于這一目的。面對這一無可逃避的歷史必然性或命運,中國人的這一選擇,不管是被迫還是自愿,在那個特定的時代都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作為一個現代主權國家的地位已經牢牢地確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徹底拋棄“救亡圖存”的陳舊觀念,重新思考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文化局面。換句話說,文化在今天已經不是救亡圖存的工具,而是應該恢復其教化人性、塑造精神的地位。但要確立這種文化自主性,我們固然一方面需要拋棄狹隘的政治功利主義,另一方面卻更應該破除過去一百多年來的各種偏見,不管這些偏見是來自西方的強加,還是來自我們自己的“畫地為牢”。其中,最應該破除的偏見就是——“哲學”。這里,我們可以從西方當代學者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研究說起。
沃格林指出,在公元前五世紀前后,世界上幾大普世文明都發生過一次“存在的飛躍”(leap into being)。具體地說,這些文明都從某種“神話王國”或“宇宙論帝國”(cosmological empire)突然“飛躍”到“存在的秩序”(order of being)。促成這種“飛躍”的,在希臘是以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等為代表的哲學家,在希伯來是以先知為代表的啟示神學,在中國則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沃格林在早年時期尚執著于“西方中心論”,認為中國的“存在的飛躍”與希臘和希伯來相比并不徹底,仍然殘留著“神話”和“宇宙論帝國”的痕跡。但是當他真正接觸了中國思想之后,卻產生了很大的困惑,因為他發現,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思想雖然既不是哲學,也不是啟示神學,但卻絲毫沒有神話的痕跡,在“存在的飛躍”上跟希臘和希伯來一樣徹底。這一發現不僅中斷了他的研究思路,而且對他的思想轉向產生了很大影響,使他從早年的“西方中心論”轉向了晚年的“文明相對論”。
沃格林的困惑相當有意義地表明:中國幾千年的思想傳統完全擁有自己獨立的問題和展開道路。如果不是過去一百年同西方偶然產生接觸和碰撞,那么中國人完全不需理會中國思想究竟是不是哲學之類的偽問題,更不必為所謂的中國哲學之合法性問題憂心忡忡。說中國沒有哲學不能證明中國思想的恥辱,說中國有哲學也不能證明中國思想的光榮,因為從根本上講,中國思想自古就同所謂的哲學毫不相干。要想消除“中國哲學”的學科焦慮意識,要想真正地確立中國學術的文化自主性,我們不僅需要清醒地檢討這一百多年來西方強加給我們的各種現代性偏見,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更應該徹底破除那種以西方他者為絕對參照來不斷自我審查和自我懺悔的“奴隸道德”。
吳增定:北京大學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