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飛舟:一本與一體:中國社會理論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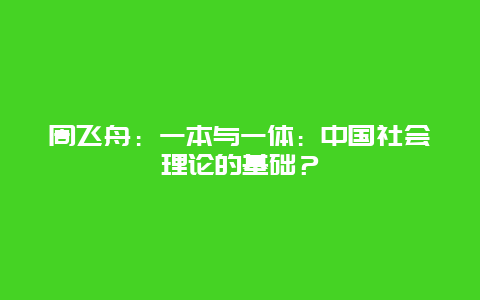
摘 要:本文是對建立中國社會理論基礎的一個嘗試性探索。近年來,關于當代中國社會的經驗研究在處理社會關系、社會結構方面的問題時難以深入,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理論認識,這也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的瓶頸。本文從中國傳統的家庭理論入手,以費孝通提出的“反饋模式”為切入點,深入討論父子關系的性質,并以此為基礎形成對差序格局和中國社會關系的基本理解。本文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基礎是“一體本位”而非“個體本位”。一體的思想源于“一本”的社會意識,即以父母為本而非以天為本或以神為本,這在中國傳統的祭禮中有明顯體現。“一體”是指“父子一體”“母子一體”,這種深層的社會意識在中國經典文本中有突出表現,本文對與此相關的儒家典籍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和闡釋。“一本”和“一體”的社會意識構成了以“孝”為本的社會倫理體系,與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相互呼應。在這種社會結構下,孝并非一種私德,而是一種具有基礎作用的“公德”,孝是眾德之本,一個真正的孝子也會是一個忠臣。“孝”背后的一本和一體意識也是我們理解差序格局概念以及當今諸多社會現象的理論基礎。中國社會轉型的根本取決于這種深層的社會意識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結構的轉型。
當前中國的社會學研究面對艱巨的理論建設任務,表現為各種關于社會學本土化、中國化和中國話語等主題的討論。這些討論并非完全出于意識形態的需要,而是更多來自于經驗研究的壓力。經驗研究發現的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和社會機制難以用西方的社會學理論進行深入、貼切的理解和解釋,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論產生的“水土”有異。西方的社會學理論產生于資本主義興起的時代,其問題意識、立言宗旨來自于工業革命引發的社會變革,帶有較為強烈的個體化、理性化的理論預設。在這類理論視角下,中國社會在總體上被看作傳統和非現代的,在社會結構和社會機制方面的主要表現就是“關系”仍然起支配性的作用。在以“關系”為主的社會中,既缺乏具有獨立權利和責任意識的個體,也缺乏連接個體成為“團體”的公共規則和制度,中國社會遂被看作既無真正獨立個體又無真正共同團體的“一盤散沙”的社會。這些“散沙”靠“關系”產生各種各樣的社會聯系,而這些聯系又被看作滿足個人欲望的自私狹隘、攀附結黨的工具。這是站在西方社會理論的立場上很容易形成的對中國社會的看法,而且,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主導著中國當代社會的研究。在社會學對產權、抗爭等主題的研究中,“關系”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些中國特色的概念,如“關系產權”“關系控制”等,都是從中國現實的水土中生長出來的本土概念。但這類概念普遍帶有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基本預設,很難構成中國社會理論話語體系的主干。具體而言,這些概念背后大多都有一個“理想”的標準,即“產權”“控制”本身就應該是基于個體權利和公共表達的產物,前面加上“關系”二字,雖然是對社會事實的客觀描述,卻隱含了從理論出發的批判態度。從社會學的歷史來看,對“關系”的研究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關系”的污名化過程,這個過程除了將西方社會理論作為“關系”的基本預設之外,還將“關系”理解為破壞個體獨立和公共規則的“找關系”“搞關系”,把“關系”與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割裂開來,無視“關系”在傳統社會中的結構性作用。即便一些學者已經認識到“關系”在傳統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將其作為解釋中國社會何以保守和落后的影響因素而進行批判。
“關系”在傳統社會中叫作“倫”或“人倫”,“倫有二義”,指“類別”與“關系”,“關系”背后的行動原則叫作“倫理”(潘光旦,[1948]2000)。人倫是社會結構之本,倫理則是價值觀念之本,梁漱溟(2005)將中國社會稱為“倫理本位”的社會。因此,如果要深入討論“關系”的本質,就要討論其基本的性質與預設,而這些基本的性質和預設應該基于在中國漫長的歷史傳統中形成的理論和實踐形態。這是本文試圖做出的努力,也是為“關系”正名的第一步。
人有五種主要的倫,分別為父子、夫婦、兄弟、君臣、朋友。在這五種關系中,前三種都是家庭關系,后兩種乃至其他如師徒、東伙、同鄉、同年等,都被看作家庭關系的延伸。在這些家庭關系中,父子之倫又是我們認識“關系”性質的核心和“底色”,本文的分析即從“家”開始。
“垂直”的社會結構
“家”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重要性。有社會學家說,要想認識中國社會而不認識中國的家庭,就好比要一個人進屋里來卻先把門關上(潘光旦,[1947]2000)。家庭之所以在中國有特殊的重要性,是因為家在社會結構的意義上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礎。古人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家是國和天下的“本”,人與人、群體與群體、組織與組織之間的連接都是以家庭的連接為根本。所謂“本”,就是指人們在家中的思想行為方式和家中的各種關系會“蔓延”至家庭以外,成為我們理解整個社會的底色。這與西方社會以“個體”為本位,以“團體”為形式的社會結構有很大差別。
自民國時期以來,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反思逐步由表及里,深入到社會結構的層面。梁啟超首先指出中國人缺乏“公德”,并以倡公德、倡“新民”作為改造社會、挽救中國之本。與西方社會相比,中國人缺乏公共觀念、國家觀念、平等精神和法治精神,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私”。之所以形成這種“私”病,是因為中國人缺少“集團生活”而主要依賴家庭生活。西方人的社會以各種職業、政治、宗教團體為主要形式,團體之間界限分明,團體內部公共責任和個體權利也是界限分明,這一方面塑造了公共觀念和平等精神,另一方面又加強了個體的獨立意識。中國人則是以家庭為主,工作、生活都是為了家庭,家庭成為人生的主要目的和意義所在。西方人的節慶活動主要以朋友聚會為主,雖然經常在家里舉辦,但參加人員遠不只家庭成員。而中國人的節慶日都以家庭團聚為主,有家庭成員以外的人參加是很奇怪的事情。那么,與團體生活相比,家庭生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又是如何塑造了中國人的“私”?
中國人的家,最主要的特點可以概括為:既無團體,又無個人,只有“關系”。所謂“無團體”,是說中國人的家沒有明確的界限。中國人說“家”或“家人”,并不是以戶口本為準,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范圍。下班的時候“回家”和過年“回家”,為家人“掙錢”和向家人“借錢”,這里所說的“家”和“家人”都不一樣。在有些情況下,家的范圍可以擴得很大,所謂“一表三千里”,甚至有些和自己沒有血緣或親緣關系的人也被看作“家里人”。如果沒有固定的范圍和明確的界限,家的“公共領域”就很難形成,人的“公共責任”也就難以界定。所謂“無個人”,是說中國人的家庭缺乏獨立的個體意識及個體權利。雖然在理論或法律上可以給出明確的家庭成員及其權利和責任的界定,在實踐中卻常常是“清官難斷家務事”。所謂“難斷”,是指難以使糾紛雙方心服口服,判定后難以維持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所謂“只有‘關系’”,是說中國人的家庭生活主要是在處理各種“關系”。由于“無團體”“無個人”,所以這些關系表現為如費孝通([1948]2009)所說的水波紋式的“差序格局”,即以自己為中心,層層疊疊地向外擴散。最核心的是父子、夫妻、兄弟關系,再往外有祖孫、婆媳、伯叔,乃至侄、甥,以及堂、表等種種關系。在這些關系中,人們雖然不會形成明確的個體意識和團體意識,卻會具有強烈的“關系”意識,即依據各種各樣的關系來決定自己的態度和行為。這背后當然也有權利和責任,但關系不同,其附帶的權利和責任就會發生改變,比如,父親對兒子的責任與丈夫對妻子的責任完全不同,所以,一個人的權利和責任在家庭內就是多重和不斷變化的,這與兩個概念在西方社會的含義很不相同。具體而言,權利和責任本來的含義是基于個體或者人的基本權利,雖然不同的社會角色具有不同的權利和責任,構成角色規范和角色期待,但各種社會角色的規范和期待背后存在一個“公約數”,即作為一個個體的基本權利和責任。而在中國,在作為社會結構基礎的家中并不存在這樣的“公約數”。如果父親被視為不“慈”或者兒子被視為不“孝”,他就失去了在家中的基本尊重,也不被認為還有其他的權利和責任。這種關系取向的意識,雖然也會使中國人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在西方個體/團體的視角下卻會被看作“私”,是將自己對“關系”的責任置于普遍、基本的個體/公共責任之上。實際上,在中國社會,人們對于普遍、基本的個體/公共責任并不明確,也缺乏一些基本的共識。
通過討論中國人的家而得出中國人“私”的結論,只是要解釋中國為什么相對于西方社會的“公”是落后的,卻不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社會的結構秘密。一個歷史悠久、穩定廣大的社會如何能建立在“私”的基礎上?如果作為中國人生命核心的家庭生活使中國人“私”,那么家庭以外的社會何以可能?正如韓非子最早所指出的,“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韓非子·五蠹》),一個人如果是個孝子,他就會因為父親而背叛君主;一個君主的忠臣,非常可能是個不孝的兒子。孝子慈父真的會對家以外的社會結構起到瓦解的作用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從家庭作為一種社會組織的功能入手。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一書中指出,家庭的首要功能在于為社會培養合格的成員,要為社會解決“個人有生死,社會須持續”的問題。要完成這種“社會繼替”的功能,需要夫婦雙方組成家庭來展開雙系的撫育工作(費孝通,[1946]2009)。所謂“合格”的社會成員,是指家庭不但需要生產、養成社會的成員,還需要將基本的社會文化“傳遞”給這些新的社會成員,實現“社會”在個體生老病死中的不斷綿續。這樣的社會繼替,類似于一種親代和子代間的“接力”,家庭中的許多安排和制度都是為了這種“接力”而形成的。這種“接力”的功能是家庭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理由,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社會,皆是如此。費孝通指出,西方家庭以這種“接力模式”為基本形式,但中國的家庭在親代對子代的“接力”之外,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功能,即子代對親代的贍養功能。費孝通([1983]2009)將這種“親代撫育子代,子代又贍養親代”的模式叫作“反饋模式”,“接力模式”的西方家庭“不存在子女對父母贍養這一義務”。
“接力模式”和“反饋模式”反映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繼替”的方式,是兩種不同的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模式。在接力模式中,父母養育子女是在盡一種社會責任,雖然在生育時沒有征得子女的同意,卻需要通過結婚的方式組成家庭來征得“社會”的同意。撫育既非與子女的契約,亦非對子女的恩情。子女長大成人后投身社會,以獨立個體的形式成為社會團體的成員來為社會盡責,就是對父母撫育之恩的回報。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中,父母和家庭只是子女成長的憑借和手段,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得以不斷繼替的“制度”。個人在成長中形成的人格會在社會團體,以及與社會的不斷沖突中變得獨立而成熟。在反饋模式中,父母組成家庭和生育后代卻不被看作一種社會責任,而是一種“家”的責任,是為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禮記·昏義》)。結婚、生育是為了尊祖敬宗,而尊祖敬宗的最好方式就是將子女撫育好。所以,家庭不是子女成長的憑借和手段,子女成長反而成為尊祖敬宗和家族綿續的憑借和手段。在個人、家庭、社會三者的關系中,個人以家庭為目的,社會可以理解為家庭的擴大或擴大了的家庭,這被有些學者稱為“家庭本位”(馮友蘭,
2024)。家庭本位的社會結構與個體本位或社會本位的社會結構有顯著不同。家庭本位的社會培養出來的社會成員對于社會本位的社會來說就是不合格的,或者說是“私”的,但對于家庭本位的社會結構來說未必如此。那么,家庭本位的社會結構的重要特征究竟是什么呢?
費孝通在回顧自己的學術成就時,認為自己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發現了這種社會的結構性特征,這集中體現在《生育制度》里:
然而,當我特別被涂爾干的“集體意識”概念吸引的時候,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發覺有必要把他的概念轉成垂直的。他的概念像是一個平面的人際關系;而中國的整合觀念是垂直的,是代際關系。在我們的傳統觀點里,個人只是構成過去的人和未來的人之間的一個環節。當前是過去和未來之間的環節。中國人的心目中總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孫,因此一個人的責任是光宗耀祖、香火綿綿,那是社會成員的正當職責。那是代際的整合。在那個意義上我們看到社會整體是垂直的而不是平面的。(費孝通,[1987]2009:427)
在費孝通看來,“家”的責任就是“社會成員的正當職責”,在家之外沒有一個單獨的“社會”,因為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整合觀念”不像西方社會那樣在個體/社會的平面上展開,而是“垂直”的“代際關系”。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單位,并非兩個個體的平面互動關系,而是父子、母子間的縱向關系。費孝通([1998]2009:387-388)另外又提到:
中國社會的活力在什么地方,中國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間。一個人不覺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緊的是光宗耀祖,是傳宗接代,養育出色的孩子。
這種垂直關系的核心表現就是其互動方式與平面關系有差別。因為垂直關系的首要問題是關系中的兩人地位不對等,父子、母子之間都不能將對方視為與自己“對等”的個體。我們如果用西方二人互動的關系模式來理解這種垂直關系,則不是理解為相互合作的平等模式,就是理解為相互沖突的支配模式,因此,或者將父子關系理解為與其他社會關系類似的平等而松散的關系,或者將其理解為父權支配。在中國這種以垂直關系為基本單元的社會里,垂直關系并不是一個二人互動的對子關系。父親是仿照自己的父親對待自己的方式來對待兒子,而兒子亦是仿照自己父親對待祖父的方式來對待父親。每一對關系中的個體不只是以個體的利益和權力作為準則而行動,也不只是以對方的利益和權力作為刺激而反應,還需要參照另外一對關系中的個體行為來展開,而這兩對關系只是由三個人組成,而且都是“垂直”的“代際關系”,具體如圖1所示。
圖1中的虛線為“實線關系”所參照的關系。首先,一個人的行為規范和責任是參照自己父親的行為規范和責任來展開的。在差序格局中,關系不同,所要求的責任和行為規范也不同。即使對于同樣的關系,也不存在一些固定的責任標準,因為別人家的關系不能作為自己家關系的參照標準。不同家庭的“父親”性情各異,做法也千差萬別,關鍵要在實踐中“盡心”。對于家庭中的實踐來說,無論是對待父親還是兒子,自己父親的行為都是一個最親切、最生動、最有影響力的標準。所以,一個人如何“做人”,父親的行為是模仿和參照的標準,而不是互動的對象。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父母足夠孝順,那么他自己的孩子也會是一個孝子,這與他對自己的孩子有多么好并無太大的關系。在中國,很多父母對自己的孩子非常嚴苛,但這并不意味著孩子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自己,所以有“棍棒之下出孝子”之說,因為對孩子有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的是父母對待孩子的祖父母的方式。其次,這類行為規范和責任一定要通過至少是三代人的垂直關系才能明確體現。尤其是對于“孝”的責任,一個出生在核心家庭的孩子是缺乏這樣的參照標準的。因此,中國傳統強調“孝”的觀念隱含了對于“家”的基本概括,即完整的家至少在其某一生命周期內包含了祖孫三代。這一點構成了我們對三代直系家庭在中國頑強存在的一個理論理解。第三,“父慈子孝”這種理想的規范和責任看上去像是父與子互動的結果,其實不然。五四運動以來,許多學者把“子孝”看作對“父慈”的回報,或者看作一種“報恩”行為,因而得出“父不慈則子不孝”“父不養則子不報”的結論,或者用父對子沒有“恩”來否定“孝”的合理性,這實際上都是用西方兩個個體互動的觀念來看待中國社會關系的基本單元。按照這種觀念推論,當然也可以說“子不孝則父不慈”,但這無論在中國的歷史中還是現實中,都明顯是不成立的。所以,父子關系不能當作一個對立統一的對子關系來理解,而應該理解為“父慈子則子慈孫,父孝祖則子孝父”的兩個不同序列的傳承關系的描述。
從圖1來看,兒子會不會孝順自己,以及最終會怎樣孝順自己固然和自己怎樣對待兒子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怎樣對待自己的父親(即兒子的祖父)。這個道理我們用父親對待兒子的“慈”來看就更加明白。父親對待兒子并不以兒子孝不孝來衡量,而大多是從自己的父親怎么對待自己出發,和兒子是否頑劣關系不大,這就是“學做人”的基本內容。因此,父子關系作為中國社會關系的基本單元,作為反饋模式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不能單獨割裂出來進行理解。這個關系本身就蘊含著“反饋模式”的基本要素,我們用費孝通的語言和符號將“反饋模式”展開,就得到圖2:
圖2反饋模式的部分是費孝通的圖,為了分析而將其擴展到六代人。用F來表示世代。為了清楚起見,畫了分別以F3、F4、F5為核心(“自己”)的反饋單元。以F4為中心來看(見反饋單元2),則完整的父子關系(F3→F4和F4→F5)“向上”嵌套于F3對F2的“孝”與F3對F4的“慈”。每一個“反饋單元”是由四個父子關系單位組成,隨著世代推移,這些反饋單元首尾交疊,層層“向上”嵌套,構成了費孝通所說的“反饋模式”。
從上述分析來看,向“下”的“慈”與向“上”的“孝”也不是孤立的兩個系列。孝的內容是不斷向“上”看,以父、祖為重,而就父、祖本身而言,則更向下關注子孫的狀況,謂之“慈”。“孝”要求以父、祖之心為重,所以對父、祖的“孝”的實際內容除了奉養愛敬之外,還有一個撫育子孫、綿延后代的責任,也就是說,“孝”中包含了“慈”,無“慈”不成孝,同時無“孝”也不成慈,這是在至少祖孫三代的序列中理解的結果,只用一對父子關系是得不到這樣的結論的。這中間的詳細分析可參見筆者的《慈孝一體》一文(周飛舟,2024),此處不再贅述。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家庭培養出的社會成員仍然以家庭而非社會作為“本位”,其核心內容在于對于他人的基本意識和倫理觀念是指向祖先、父母以及子孫的,具有這樣“垂直”關系意識的社會成員如何對待家庭以外的社會成員是我們理解中國社會結構特征的核心問題。要深入理解這個問題,我們仍然必須從傳統理論出發,去追尋這種垂直的關系意識的本。
一本
費孝通所說的“垂直”的“代際關系”,是指個人的一種根本性的社會意識,即個人不是將自己看作社會的一分子,而是首先將自己看作連接過去的人和未來的人的一個環節,過去和未來的人并非普通的社會成員,而是自己的祖先和子孫。這種意識源于中國傳統中的“一本”思想,涉及深層的天人觀。我們需要對其加以較為深入的討論,才能理解其理論構成。
“一本”的具體說法來自《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以“兼愛”“薄葬”為基本主張的墨家學者夷之與孟子有一番通過孟子的弟子徐辟在中間傳話的“隔空”辯論。作為儒家學者的孟子對墨家的薄葬很不以為然,指出夷之雖然主張薄葬,但他言行不一,在葬自己的父親時用了厚葬,這種行為也與墨家的“兼愛”主張相矛盾。夷之反駁說,儒家即使講究有差別的“仁愛”,不是對普通百姓也會說“若保赤子”嗎?墨家講究無差別的“兼愛”,但具體施行起來,當然也是從身邊的親人開始,這叫做“愛無差等,施由親始”。由此可見,儒墨兩家也無根本的區別,都是主張大同博愛之理,只不過儒家強調從身邊做起,墨家強調愛兼天下,有體用之別而已。孟子對這種從根本上援儒入墨的說法進行了反駁:
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他日過之,狐貍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于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孟子·滕文公上》)
“赤子匍匐將入井”一句,是孟子反駁夷之錯誤地引用儒家經典《尚書》中“若保赤子”的話。《尚書》中的意思是說,殷之小民無知而犯法,是被紂王欺騙脅迫,陷于惡而不知,就像小孩子匍匐在井邊一樣需要救助,并不是說保護普通百姓和保護自己的孩子沒有差別。孟子反問夷之:你真的認為人們愛自己的孩子和愛鄰人家的孩子沒有差別嗎?孟子此處所講的愛,并非一種純粹自然或實然層面上的愛。雖然在自然或實然的層面上愛也具有這種差別,但自然或實然層面的差別只是夷之所謂“施由親始”的差別,是一種由于人的能力和時空限制帶來的具體操作上的差別,與應然的超越層面一視同仁的“愛無差等”并不矛盾。這是夷之的理論而并非辯論時的遁辭。但孟子談愛說性,是緊隨孔子說“仁”而來,并非僅在自然或實然層面論說。所謂“彼有取爾”,并非實然層面上僅就親疏遠近和是否可及而導致的差別和選擇,而是說明這種差別和選擇在超越層面也有當然的正當性(牟宗三,2024)。人們在現實的行為層面雖然有這種差別,但這不是孟子所強調的重點,他強調的是人在超越層面也仍然有這種差別。他用另外一個例子說明了愛的差等具有一種超然的正當性。
孟子說,在上古時期,由于禮制不備,人們并不一定會認真埋葬自己的父母。有的人父母死了,會委之于溝壑,就像對待和自己無關的人的尸體或者其他動物的尸體一樣。這是在實然層面的舉例。在這個層面上,許多人都會對父母有生不孝養、死不安葬的行為,也就是對待父母與對待他人無差別。但是,如果有人這樣做了,他恰好在不久后的某天從溝邊經過,看到父母的身體被野獸和蟲子咬得亂七八糟,他就會額頭冒汗,不忍直視。孟子強調說,“夫泚也,非為人泚”,額頭冒出的汗不是給別人看的,也沒有其他任何實際的原因,是“中心達于面目”,是超越層面的良知和良能起了作用。在這個層面上,良知、良能之所以起作用,就是因為這是自己的父母而非別人的父母。
孟子所舉的例子是一種極端情況,其極端之處在于,在實然層面此人的行為沒有差等,父母死而不葬,其良知被遮蔽得幾無蹤跡可尋。只有當父母的尸體遭到毀壞,自己親眼所見時才會有所觸動。這種觸動明顯與“施由親始”無關,
因為此人并沒有這樣做,以此證明了愛有差等是孝子仁人之“道”。用孟子的話來說,個人之所以有所觸動,是因為如此對待自己的父母不符合天理:“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對于這個“一本”的說法,漢儒趙岐(2009)注曰:“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孟子注疏》)無論是人還是其他生物,都是從其父母而出,并沒有其他的來源,這叫做“一本”。在這個概念上,儒家學者有兩種理解,偏重有所不同。
朱子強調“一本”的“一”字。人物俱生于其父母,則其父母就是一本所在,因此,無論是人還是動物,都有自己的一本。一本的重點在于“各”有其本,不能混淆。別人的父母是別人的本,而不是自己的本。所以,雖然人物各有其本,但對每個人來說,本只有一個,其他的都不是本。否則就會犯“二本”的錯誤。在《朱子語類》中,朱子和弟子的討論詳細地闡發了這個觀念(黎靖德,1986)。
或問“一本”。曰:“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個一樣重了,如一本有兩根也。”
問:“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有本末也。所謂‘二本’是如何?”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退與彥忠論此。彥忠云:“愛吾親,又兼愛他人之親,是二愛并立,故曰‘二本’。”(《朱子語類》卷五十五)
將自己的父母和別人的父母同樣看重,便是二本。在第二條《朱子語類》的材料里,朱子延伸了對“二本”的理解,認為若“愛無差等”,則普天下的父母都是本,所以也可以認為是“千萬本”。既然可以將其他人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都看作本,那么所有的生命都可以看作本,既可以說“千本萬本”,也可以說根本上是“無本”。
“千萬本”或“無本”的理解是從“愛無差等”的表現來說的。“一本”和“千萬本”,在這個層面上好像還只是視角的差別,即從自己的視角看,是“一本”,不從自己的視角看,則“千本萬本”。但這背后還有更深入的理論問題,即此“一本”或“千萬本”背后是否還有一個更根本的“本”的問題。明儒王夫之(2011)更為深入地分析了墨家的“二本論”觀念:
天者,人之大本也,人皆生于天,而托父母以成形,父母為形之本,而天為神之本;自天而言之,則我與萬物同本而生,而愛不得不兼。神受于天而貴,形受于父母而賤,故棄親而薄葬。(《四書訓義》卷二十九)
古人認為人的生命由形和氣組成。氣之盛者為“神”。王夫之將墨家的“二本”理解為“形之本”與“神之本”。就神而言,以天為本,而天對萬物俱有生生之德,一視同仁,故愛無差等;就形而言,以父母為本,而形體有時間、空間之局限,故施由親始。但神受于天而不滅,形受于父母而暫存,故神形合一而有人,形只是神暫時居住的軀殼而已。由此而言,雖言“二本”,但貴賤懸殊,父母只是天生人物的憑借和手段而已。父母對自己的生育和撫養,如同其他有助于人身長成的食材、織物一樣,都是為短暫的身形而設,并無長久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看,即使父母對自己有恩情,這種恩情也與食材、織物的作用一樣,人們只是需要以利用和感謝食材、織物一樣的態度感謝父母即可,真正的恩情來自于天。因此,在天與父母面前,墨家的觀念看似“二本”,實際上也是“一本”,是以“天”為本。所以,從王夫之的分析來看,儒家、墨家的關鍵區別不在于一本和二本,而在于到底是以父母為本還是以天為本。
孟子說,“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既然用“使之”二字,則天并非“本”顯而易見。朱子集注曰:“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此最能得“使之”二字之真意:以自己父母為唯一的本,是天理。或者說,天生育萬物的方式就是使萬物各自生于其本,是以其本為本。至于天生萬物,萬物生于天而不以天為本,需要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天”的概念在殷周之際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根據余英時(2024)對“天人之際”問題的梳理,天不再是有喜怒哀樂和明確意志的“人格天”,也沒有變成如近現代所理解的包含規律和萬物秩序的“形上天”,而是介于二者之間。天的主要作用在于“生生”,“生生”中包含萬物生育之機,也蘊含以“生生”為核心理念的“天道”,此之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的“仁”,孟子的“性”,雖然都是聚焦于人倫日用和人的生命過程,但其內在的超越性和生發力皆上貫于“天”和“天道”。這種天道與人道的貫注和聯結,并非將“天”或“天道”神化或人格化以宗教的方式實現,而是以道德形而上學的方式實現。對于孔孟程朱等思想家而言,天人關系的核心是人通過道德實踐與天道達成一種所謂的“內在的遙契”或“內在的超越”(牟宗三,2024)。人以天道為目標,但重點在于這個道德實踐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思想的主流被認為是“人本”或“人文”的,而非以“自然”或“神化”的天為本(潘光旦,[1931]2000;錢穆,2012)。但是,以人為本又極為關注天道,所以在思想和哲學層面,以“天人合一”為基本觀念,以“天人之際”為基本領域,不斷討論盡心知性和樂天事天是思想家的主要理論問題;而在實踐層面,這種天人之間的貫注所形成的是一整套以孝和敬為核心理念的禮的體系,這套體系的核心是祭禮,其背后的基本觀念就是一本。所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記·郊特牲》),是說一本之“本”本乎祖而非本乎天,是祭禮的關鍵所在,這需要對祭禮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中國傳統的祭禮雖然處理的是天人關系的問題,但其主要祭祀的對象并非天,而是鬼神。在祭祀體系中,只有天子的禘禮是“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禮記·大傳》鄭注)。天子其他的祭禮,以及諸侯、卿大夫、士的祭禮,都不能祭天。天子祭天,亦并非將天作為其“本”,其本仍是先祖,故“以先祖配之”。《禮記·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鄭玄注曰:“言俱本,可以配。”(《禮記正義》)意思是天為物本,祖為人本,俱是本,故可以祖配之。即使天被視作“本”,也只是天子一人之“所自出”的根本,而不是其他人的“本”。諸侯及卿大夫除祭祀山川、社稷、五祀之神外,其主要的祭禮還是祭祀祖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二廟或一廟所祭祀的都是歷代祖先,亦稱為神。所以,就祭祀的鬼神而言,分為山川、社稷、五祀等神祇與祖考。山川社稷等神屬于各有職司之神,雖然分屬于諸侯、卿大夫之國與家內,其司職卻相當于官職,而真正與人的“本”有密切關系的是祖考之神,因為他們與人的生死有密切的關系。我們在此需要對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鬼神理論進行討論,以進一步看清“一本”的觀念到底扎根在何處。
古人對生死和鬼神的理解一般認為最早見于《左傳》中“伯有為厲”的記載。子產為其立后,伯有之鬼即被安撫平息。子產在解釋為什么伯有死后會變成鬼時說: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于人以為淫厲。況良宵(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其用物宏,其取精多,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春秋左傳正義·昭公七年》卷四十四)
子產這段話的大意是說,人生先有魄,后有魂。如果生前生活條件好,魂魄就會比較強大。一般的人如果死得不正常,魂魄就會變成鬼來影響人。伯有是貴胄之后,又是高官,生前魂魄強大,又死于非命,所以會變成鬼。這段話包含了中國古人對生死和鬼神的基本理解,后來儒家思想的有關解釋基本沒有超出這個范圍。
人生始于魂魄的結合,死于魂魄的離散。人生先有四肢百骸的形體,形體之上的覺識聰明叫做“魄”;然后有噓吸出入之氣,氣之精華叫做“魂”。形、氣側重于“身”,分別指四肢百骸和噓吸出入,魄、魂側重于“心”,分別指身體器官以及呼吸氣息所帶來的能力和意識,是“形之精”“氣之精”,用現代的語言說,可以叫作精神或“情識”(錢穆,2011),包括一個人的音容笑貌、思想氣質等。如果進一步辨析魂魄之別,則魄為形體之功能,如目之有明、耳之有聰、口之能言與鼻之能嗅,如手之能持與足之能行,即人的知覺運動;其視聽言動的極致為“魂”,即所謂“陽曰魂”,集中表現為人心的虛靈不昧。人心既虛靈不昧,則可以“具眾理而應萬事”(《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朱熹,1983),此心一方面受既有之宇宙人文世界的滋養,另一方面又與人之知覺聰明相互映發,猶如日光耀月而有月之明,以車載人而有千里之行,月與車雖為陰與靜的一方,但月的映發之體質,車的聯動之機括實在是不可缺少的一端,日月合一,人車合一才有精一之妙(《楚辭辯證·遠游》)(朱熹,1979)。如此而言,魄是魂之體,魂是魄之用,體用相合,人的精神情識才會湛然若神。這是強調神生于形、形神兼備、陰陽和合的理論,與靈魂肉體的“二分論”有很大差別。
魂魄合一而生,分離則死。人死后,形歸于土,其精為“鬼”,氣發揚于上而為“神”,因此,人死后有個“魄”化為“鬼”和“魂”化為“神”的過程。人始死時之“復”禮,即是招魂,此后使其暫安于“重”之上。葬禮的重要過程是處理體魄的過程。葬禮中頻繁的奠禮用于安頓體魄,直至下葬后“迎精而反”(《禮記·檀弓》),即形體藏于地下,而精魄迎回祖廟,與神魂合受祭祀,這個禮叫做“虞”,是從葬禮到祭禮的轉折點。神與鬼在祖廟中憑依于神主接受后代的祭祀,才能安定下來而不憑依于活著的人作亂,這是子產之所以能夠安撫伯有之鬼的原因。
子產并沒有說明為什么“為之立后”就能安撫厲鬼,似乎這個不用解釋,是當然之事。在《禮記》中,宰我問孔子“鬼神”和祭禮的關系的時候,孔子回答說: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禮記·祭義》)
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玄注曰:“合鬼神而祭之,圣人之教致之也。”(《禮記正義》)孔穎達疏解說,魂魄和合則生,死而分離為神或鬼,圣人因此設此禮“聚合鬼神,似生人而祭之”,就是使死后分離的魂魄(鬼神)能夠重新“聚合”,就像生前的狀態一樣。做到這一點的辦法就是子孫施行的祭禮,這也是祭禮的意義所在,所謂“事死如事生”是也。在祭禮中,子孫齋明盛服,聚精會神,鬼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這本身就是一種感通忘我的神明狀態。
我們就此更深入地討論一下祭祀時的狀態來說明古人對鬼神聚合感格的理解。古人認為,祖先之鬼神能夠來格,應該至少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是自家的子孫。祭禮的大忌就是“非其鬼而祭之”,孔子譏其為“諂”(《論語·為政》),《左傳》云“神不歆非類”,朱子說得更加明白: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個氣,所以才感必應。(《朱子語類》卷三)
感應的基礎是“一個氣”。從天地總體而言,“只是一個氣”;就萬事萬物而言,這個“氣”有具體的遠近親疏之別,祖考子孫之氣更是“一個氣”,更加容易感應。第二個條件是子孫必須保持必誠必敬的精神狀態。孝子將祭,致齋于內,散齋于外,盡其愨信,洞洞屬屬,見以蕭光,加以郁鬯,上下用情,不敢弗盡,才能“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朱子語類》卷三),
才能進入洋洋乎如在左右的狀態。這種感格的原理,宋代學者黃榦有深入而精妙的解說:
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摶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于舜之樂哉?今乃以為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于指也,可乎?(《勉齋先生黃丈肅公文集》卷第十四,“復李貫之兵部”)
黃榦的意思是說,舜的《南風》之奏已經不能再聞,但其曲中所寄之精神情識長留天地間。絲桐之琴常在,善奏之妙手代有其人,如果真能體會舜之精神情識,《南風》之奏不也能以某種形式再現嗎?祖考之音容笑貌、道德猷為俱已逝去,但所以為其道德猷為,所以有其音容笑貌者,自然留存于天地之間。子孫本具祖考之形貌氣質,熟悉其道德猷為,若能善繼其志,善述其事,祖考之鬼神難道不能真的合于孝子順孫之身而僾然肅然,見乎其位,顯乎其容聲嗎?用錢穆(2011:11)的話來說,這“不啻為所祭者之一番復活”,即子孫之祭祀,為祖考永生和不朽之憑借。這種不斷的“復活”,與子孫的生命狀態緊密聯系在一起。子孫慎終追遠,不斷體驗到生命的延續,在生命的延續中意識到自己的“本”。這個“本”,不但是自己生命的來源,也是自己生命的意義。自己的生命承接祖考的生命,還要用子孫的生命繼續傳承下去。“生命乃自生命中來,亦向生命中去”,以生命承接生命,乃有“身生命”的相續和“心生命”的永生(錢穆,2011:163-165),這就是個人的生命作為連接過去和未來的一個環節而永生,此之謂“一本”。
一體
祭禮中子孫的“聚精會神”狀態是一種與祖先的“交流”,不能簡單地看作單方的想象或幻想。事實上,在當前中國民間的各種祖先祭祀中,這種“交流”雖然形式各異,但祭祀者本人常常將其作為一種與祖先“交流”的特殊方式。根據上一節的討論可知,這種交流基于“一本”意識,有其“形氣論”的物質基礎:子孫與祖先形體同源,氣脈貫通。祖先雖然形體已逝,氣亦消散,但其精神仍然會與有同源、同質形體氣脈的子孫發生感通,這被看作祖先生命的延續。前面所引黃榦的話更加強調了這種“交流”的精神基礎:除了形氣相通之外,還必須有一番必誠必信、虔敬愛慕的孝心,如果是“不肖子孫”,則不能期待祖考來格。祖先生命的延續,實際上是子孫“孝”的延續。
《論語》中孟懿子問孝,孔子對曰“無違”。此后又對樊遲解釋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死后的葬與祭仍然是“孝”的一部分。“孝”被看作子孫的責任,是子孫一種極為重要的生命狀態,并不因父母的去世而終止。
在中國傳統社會,“孝”的最高人格典范是舜。舜有瞽父、后母和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象,所謂“父頑、母囂、象傲”(《尚書·堯典》)。三人聯合起來幾次想要害死舜但都沒有成功,而舜仍然“克諧以孝”。根據《尚書·虞書》的記載,舜在被選定為天子繼承人后仍然履行一個兒子的職責,躬耕于田。在《孟子》一書中,孟子的弟子萬章對于《尚書》中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一條記載有疑問,不明白舜為什么在田野中大哭,由此展開了一番問答。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曰:“長息問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孟子·萬章上》)
孟子對于舜在耕田時哭泣的解釋是“怨慕”。朱子在集注中解釋為“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對于“慕”這個字,鄭玄在《禮記·檀弓》中對經文“其往也如慕”的“慕”字解釋為“小兒隨父母啼呼”(《禮記正義》卷七),是小孩子以為父母不要自己時的求之不得、求之不已的狀態。孟子認為,對于自己不能得到父母的歡心這件事,舜始終無法釋懷而怨慕不已。萬章仍然無法理解,因為舜已經克盡子職,父母仍然不喜歡,就不應該有所怨慕了,畢竟自己已經盡力了,這時候應該“勞而不怨”。孟子引用曾子的學生公明高與其弟子長息的對話來回答。長息也有與萬章相似的疑惑,不能理解舜為什么如此怨慕。公明高說,你理解不了也正常,因為你還沒有舜那樣的孝子之心。孝子不會因為自己盡職盡力就安心了,無論做到什么樣,只要得不到父母的歡心,孝子就會怨慕。孟子用舜的情況繼續申述這個意思。當時堯已經選定舜作為繼承人,并把兩個女兒娥皇、女英也許配給他。舜已經得到天下人的擁戴,得到最好的女人,富有天下,并即將貴為天子,得到人們想要的所有東西,但這些都“不足以解憂”。已經年逾五十的舜,在田野中仍然哭得像一個無家可歸的小孩子。孟子稱之為“大孝”“大舜”,是說舜的這種狀態才是真正的孝子的生命狀態。
人世而終止。舜的不安與哭泣揭示了人與父母的深層聯系——與父母關系隔絕,自己的生命就處于一個無本無源、殘缺不安的狀態。所謂“無本無源”,是指自身生命的“本”失去了著落,猶如斷水的河流和斷線的風箏,無法與過去的人相連接,自然也無法獲取源源不斷的生命力量;所謂“殘缺不安”,是指自己的心得不到安定,因為與父母的關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人少則慕父母”,即未成年階段不能獨立,對父母的情感狀態就是依戀和怨慕;成年以后,可以脫離父母而成家立業,則會慕少艾、慕妻、慕子、慕君;父母去世以后,自己已經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與自己父母的關系就是保持在一個祭祀的狀態。而舜是“終身慕父母”,對父母的依戀怨慕不因成家立業乃至父母存沒而改變。曾子對“終身”的理解是:“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禮記·內則》),一個人的孝不因父母去世而終止,而是直到自己去自己無法置父母對自己的討厭于不顧,這種不安并不會因為自己克盡子職、躬耕力田而有所緩解。明儒王夫之(2011)揣摩舜此時的心事,有細微的解說:
舜蓋曰:我竭力耕田以致養,不過共為子職而已矣。則是子自有職,而父母之外有子也。乃父母之不我愛,豈父母之情固然,而非我事乎?我以父母之心為心,則父母之心與我心一也。此必于我有未盡焉,求其故而不得,而窮則呼天,又極思父母,希冀其愛而不能,故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四書訓義》卷三十三)
王夫之的意思是說,耕田致養雖然是子職,但并非盡到子職就可以無憂。如果盡到子職就可以算是盡孝而無憂,而不管父母是否滿意和歡心,那么“孝子”之心與父母之心便變成了“兩個心”,父母變成了有兩個兒子(“父母之外有子也”)——盡子職的是一個,父母喜歡的是另外一個。王夫之(2011)以舜的語氣說:難道父母不喜歡我,是父母的本性如此嗎?難道和我怎么做沒有關系嗎?一定是我哪里還沒有做好,我的心在哪里還沒有和父母的心思相契合,我到底應該怎么辦才好呢?王夫之(2011)又說:“蓋天下之理皆可以職言,而惟孝則但存乎心。天人相繼,形色生命相依,生生相續,止此心也。”(《四書訓義》卷三十三)天下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用職分的責任標準來衡量,唯有“孝”必須論心而不論職。因為自己的“心”和生命都是從父母而來,所以自己的心離開父母便無所憑依和殘缺不全,自己的心和生命與父母實在可以說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可以叫做“一體”。
“一體”較為完整的說法來自《儀禮》。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儀禮·喪服傳》)父子一體,不只是說子之生命從父而來,而是強調父子的不可分離,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夫妻、兄弟也有此義。與夫妻、兄弟相比,父子之“一體”又有生生相續的意思,所以為三個“一體”之首。《孝經》開篇即云:“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這可以看作對“父子一體”之義的細致詮釋。從形體氣脈上說,子女俱受之于父母,父母將子女視為自己生命的延展和生命的一部分,子女也不能將自己的身體發膚視為己有,其一毫一發、一舉一動俱與父母生命之關切緊密相連,父母全而生之,子女當全而歸之,這是“孝”的開端;從精神覺識上說,子女亦俱受之于父母,父母將子女視為自己生命的延展和生命的一部分,子女也不能將自己的功名道德視為己有,其所作所為、功名事業俱與父母生命之期望緊密相連,子女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這是“孝”的完成。無論是“孝”的開端還是完成,以“一體”之義為基礎的“孝”是指子女將自己的身體和事業都視為父母之身體和事業的延續,是與父母“共同的”身體和事業,而不是將其視為是“自己的”或“個體的”。
由“一體”入手,我們就能夠更貼切地理解舜的號泣:舜的功名事業雖然已經達到頂點,但他認為,如果沒有父母的愛和關心,生命就是“殘缺的”。他的生命猶如樹干上長出的枝葉,與樹干分離就會枯萎。長息說“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在舜看來,殘缺的生命是不能稱之為“我”的,因此,其他的所得都不足以解憂。我們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舜對父母的愛和敬已經達到一般人做不到的地步,但舜并不是以自己做到什么程度來衡量自己的“孝”,而是以父母喜歡自己來作為“孝”的證明。只要父母對自己不夠喜歡,就一定說明自己還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夠好,但舜又不清楚還可以怎么做得更好才能使父母喜歡自己,所以才憂急如此。“大孝”的舜為中國人樹立了一個很高的標準:無論子女做了什么,只要父母不滿意,子女就不能認為做到了“孝”。與這個標準相比,“二十四孝”中的許多故事就可以理解了,子女為了父母而無所不用其極,并不一定是為了得到“好色”和富貴,而是為了自己的身心——為了父母,其實也是為了自己。
由于每個人不能選擇自己的父母,而每家又境況各別,父母性情各異,所以要讓父母喜歡,子女的“孝”就不能“以職言”而只能“存乎心”,需要以父母之身心為身心,冬溫夏凊,無微不至。這似乎很難,但父母對子女的“慈”其實從來就是如此。父母的慈愛亦以子女之身心為身心,噓寒問暖,纖毫必感。“孝”與“慈”相比之所以更加重要,與中國的文化和社會結構有關。在“一本”和“一體”的社會中,“孝”除了子女對父母的“愛”之外,還有“敬”。所謂“父子首足也”,首足不可分割意味著父子之間的愛,而父為首、子為足的比喻意味著其中的長幼尊卑之別,也就是說,“孝”比“慈”多了一個內容,即對父母的“敬”或“尊”。
愛來自于父子、母子間的骨肉血親,無論是父母對子女還是子女對父母,
皆是如此。父母對子女“唯其疾之憂”(《論語·為政》),子女對父母,則是“色難”(《論語·為政》),也就是說,子女在奉養孝敬父母之際,最難的是要讓父母覺得自己一切都很好,這是以父母之心為心;而父母對子女關懷備至,洞悉忻戚,所以“事親之際,惟色為難”(《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極深的體貼和極大的克制。朱子引用《禮記·祭義》的話來解釋孝子的容色:
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禮祭·祭義》)
這段文字最能闡發由愛生敬的理念。對于一本的祖先和一體的父母,孝子的愛必然表現為和氣、愉色和婉容,必然像捧著珍貴的玉器和盛滿的容器一樣,像玉器、容器隨時就會掉落一樣,惻怛深愛之情,必以慎重至敬出之。如果說愛是出于父子骨肉自然之情的話,那么敬則是愛的“升華”。敬是對愛的克制和反省,使得愛能擺脫其自然情欲的狀態,這種克制和反省本身就是正義的來源。在中國古代的主流倫理思想中,正義與愛一樣,不是來自于人本身以外的某種超然的存在,而是來自于對父母的尊敬。所謂“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孟子·盡心上》),敬長之義并非說父母代表了正義,或者說尊敬父母就是服從正義,而是說由對父母之深愛生發的尊敬能夠使人進入或保持一種清明誠敬、反省克制的狀態,這種狀態與人性中的善和正義能夠響應和溝通。一個以愛興敬、以敬治愛、合敬同愛的孝子就是一個最接近善和正義的人。《論語》有云: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
人以父母為其生命之本與生命之體,由此生出的愛敬亦為做人的根本。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以愛敬為核心內容的孝弟就成為所有美德的根本。在中國社會,一個人在家中的孝弟從來不被看作個人的私德,而經常被作為衡量此人對待家外的師長、朋友和同事可堪信任的標準。一個在家里對父母不好的人,即使對師長、朋友和同事再好,也不會被認為是一個好人。“夫孝者,德之本也。”(《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這個“本”是眾德之本,是從人生命的“一本”而來。
我們現在來仔細討論孝對社會結構的作用。《禮記》中引曾子的話: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于親,敢不敬乎?”(《禮記·祭義》)
孝的理念來自于“一本”和“一體”,所以孝子的一切行動就是父母行動的代表,這叫作“行父母之遺體”。意思是,無論父母是活著還是去世,孝子之身就是父母之身,去世的父母就相當于“活”在孝子的身體和行為當中,像我們上一節所分析的那樣,這正是“以生命延續生命”的“一本”理論在每一個人身上的體現。父母在世時,孝子與父母“一體”,孝子的行為體現了父母的教誨;父母去世后,孝子與父母“一體”,孝子的行為就是父母的聲譽。所謂“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記·祭義》)。可見,要做到“終”,就要立身行道,死而后已。一個人對父母再“好”,如果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如果像韓非子所說的那樣為了奉養父母而在戰場上臨陣脫逃,這恰恰是地地道道的“非孝”,因為這是給父母留下了恥辱和惡名。曾子的說法顯示了“孝”并非一種局限于家內的私德,而是一種能夠貫穿、滲透至更大領域的美德。事君忠誠、蒞官莊敬、戰陣勇敢的“公德”是建立在孝的基礎上的。
“孝”之所以能夠成為“本”,是因為其本質是“一體”而非“個體”,或是說“一體本位”而非“個體本位”。一個將自己視為獨立個體的兒子也可以做到奉養父母、尊敬父母,父母也會歡喜和滿意,但這大多來自回報、交換的意識或樸素、自然的情感。前者出于公平的理念,與市場交易沒有本質區別;后者近于憐憫的態度,與養犬養馬頗有相似之處。這樣的人,也會被誤認為是“孝”,但在關鍵時刻,就會“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費孝通,[1948]2009:130)。費孝通([1948]2009:130)注意到了這種行為與《大學》中“修、齊、治、平”的差序格局實際上是同構的,“在條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內向和外向的路線,正面和反面的說法”,由于群己的界限總是相對而非絕對的,所以會導致人向內收縮而自私。但是,一個差序的結構會導致人“私”的結論是費孝通對差序格局“以自己為中心”的預設得出的推論,這個預設是“個體本位”的。“以自己為中心”的個體在差序格局里會自私,會犧牲家、黨、國、天下是此預設下的必然推論。但“個體本位”并非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單元,許多學者對此已有論述(梁漱溟,2005;馮友蘭,2024)。費孝通([2003]2009)晚年重新提及“差序格局”概念時,也意識到了個體本位的預設存在問題,而花大力氣討論“講不清楚的‘我’”,討論“將‘心’比‘心’”,認為差序格局也是一條“推己及人”的“必由之路”,這說明他認識到了差序格局“核心層”的預設是關鍵所在。
要做到“推己及人”,必須是“一體本位”,“一體本位”才是真正的“孝”。 只有基于“一體本位”的愛敬,才能由己及人。《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孝經·天子章第二》)又云:“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孝經·士章第五》)愛和敬來自人與人之間的感通。父母與子女間的愛敬,源于尊祖敬宗之一本,匯于融合無間之一體,清明暢茂,猶如泉之豐沛而外溢,火之健旺而照物,老以及人之老,幼以及人之幼,是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以順天下的“順德”。所謂“推己及人”的關鍵,在于“己”字而不在于“推”字。在儒家思想中,“己”與“人”是相對的范疇,在內容上則講究“己”與“人”之間的感通。《論語》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此處的“己”是一個包容、開放的“己”。朱子的解釋最為切實具體:
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于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朱子語類》卷六十三)
所謂“求諸人”,就是覺得別人對不起自己,比如,父親覺得兒子對自己不夠好。所謂“求諸己”,就是用自己要求兒子的心去檢查自己,按照這個標準,自己對父親夠好嗎?自己對父親的態度與舜對瞽叟的態度相比如何?如果用這個“心”檢查自己,則“己”便變成開放、包容和擴大了的“己”,便將父親包含在“己”內而為一體。若以此“一體”之“己”去審視自己的兒子乃至別人的兒子,便是“推己及人”了。這種“推”用的是家內“祖—父—子”的三人關系結構,但可以突破家庭的限制而到達一般的社會關系層面。《大學》中在討論完“齊家”之要害在于“孝悌”后,開始論述從“齊家”到“治國”的要訣,謂之“絜矩之道”: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禮記·大學》)
所謂“老老”“長長”就是孝悌在家外的推展。所謂“絜矩之道”,其實就是“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禮記·中庸》),只是在家外演化成了一個一般性的“甲—乙—丙”的三人關系。其中,乙作為主體,對待丙的態度和行動都參照甲對待乙而在乙那里造成的感受而來。甲、乙、丙不一定有密切的關系,但作為行動主體的“乙”若能有誠心正意之德和修身齊家之教,必然能夠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的富貴窮通之境有差異,但孝悌愿欲之情有同然,絜矩之道就是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得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均齊方正。所謂 “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所悅者眾”(《孝經·廣要道章第十二》),層層推展,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正是治國平天下的至德要道。
推己及人是將自己與親人感通和理解的方式用于與他人的感通與理解。由于自己與親人“一體”,所以這種“推己”也將經常將親人、家人的情感包含在內,可以理解為“己”的擴大。若能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將他人包括在“己”的感受范圍之內,則他人的痛苦和歡樂便會引起自己的同情,這就是“仁”的核心內容了。所謂“麻木不仁”,便是指一個人缺乏這種推己及人的同情。由于人的品質、能力和社會地位有差別,所以推己及人的范圍便有大小。《孝經》中分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庶人的“孝”是“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孝經·庶人章第六》),而諸侯的“孝”是“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孝經·諸侯章第三》),天子的“孝”就是“愛敬盡于事親,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孝經·天子章第二》),便是以天下為一家了。由此可見,“一體”的理論拓展開來,并不限于父子、夫妻和兄弟,而是覆載宗廟、社稷和四海百姓。到了圣賢的境界,則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易·乾·文言》),但如此其大無外的“公德”與“大道”,與以父母為一體的“孝”是同一個倫理: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祭義》)
不以時斷樹、殺獸而被認為是不孝,并非說以天地萬物為父母,而是說一個與父母為一體的孝子會有惻怛慈柔、恒存不舍的不忍之心,仁民愛物,川流敦化,淵淵浩浩,俱來自于一本與一體之源頭活水。
余論:“一本意識”與“一體本位”
本文從考察中國人“家”的觀念入手,試圖分析和展示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與中國人基本的行動倫理。家內關系考察的第一個重要發現是,中國人的社會關系是以“祖—父—子”三代關系為基本單元,而不是父子之間的對子關系。這是在行動倫理的維度上展開的。父子之間的互動不能脫離父之父或子之子而單獨存在,即為人父的前提是為人子,而為人子的前提是為人孫,如何做父親是仿照自己的父親怎么對待自己,如何做兒子是仿照自己的父親怎么對待自己的祖父。這里“仿照”的內容是彼此對待對方的行動倫理,這背后包含了一系列以關系為前提的責任和義務,就父子之倫而言,其核心的行動倫理就是“慈”和“孝”(周飛舟,2024)。“慈”和“孝”的主要內容靠至少三人的關系框架得以實現,這構成了我們對費孝通“反饋模式”概念的詳細理解,也是中國家庭區別于西方“接力模式”的關鍵所在。
家內關系考察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是,家內的行動倫理如何與家外的社會結構相適應?這就是五四運動以來許多學者重新提出的關鍵性問題,一個家內的“孝子”如何是一個國家的“公民”?之所以說“重新”提出,是因為韓非子在兩千多年前就質疑以“孝”為核心的行動倫理,
認為它對社會結構具有破壞作用,五四運動以來的大部分學者只是舊事重提而已,連家庭本位導致“私”的討論也可以算作韓非子理論的余緒。這個問題討論的新意,是將西方“個體本位”的理論作為中國社會結構的前提預設。這樣的社會結構非但不需要“孝”這類行動倫理作為支撐,反而必須徹底拋掉這些傳統倫理,才能建設真正個體主義的社會。本文的考察旨在說明,“孝”這類行動倫理的基礎是“一本”與“一體”,這也是非個體主義的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礎。
所謂“一本”,就是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而非神本主義或自然主義。具體到行動倫理和社會結構層面,以人為本是以父母、祖先為本,古代思想的“天人觀”和“鬼神觀”都是以此為核心而展開的。以父母、祖先為本,使得中國人的生死觀沒有走向“靈魂論”或“輪回說”,而是追求“以生命延續生命”的人文理念。每個人都把自己看作連接過去的人和未來的人之間的一個環節,生命的意義便是以“始于事親、終于立身”的方式完成這個連接,這也賦予每一個人強大的生命動力。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大部分人都沒有明確的“一本”意識,但他們為了養育出色孩子的行動動力與以前任何時代相比都沒有減弱,這背后的確不只是為了盡一種社會的責任,更是在盡一種生命的責任。以父母、祖先為本的生命意識表現為以“孝”為眾德之本的倫理結構,這樣的生命意識和倫理在結構上都是“垂直的”,這是費孝通首先以社會學的理論話語表述出來的,構成了我們理解中國社會的人倫和“關系”最為堅實的理論基礎。
“孝”的社會實踐基于父子一體和母子一體的感通。一體的“孝”,不是子女以外在的正義為原則,也不是以自己的盡心為滿足,而是以父母之心為心,行父母之遺體,終身而后已。這種實踐中充盈豐沛的“愛”與清明克己的“敬”是一條最根本的修身之道,經過親疏遠近和尊卑上下的人倫關系而推以及人,老幼及天下,以天下國家、天地萬物為一體,都根源于父子、母子之一體。
“差序格局”所描述的正是這種親疏遠近和尊卑上下的圈層結構。一個人在這種圈層結構中到底是損人利己還是推己及人,并不取決于這個結構本身,或者說,中國人的損人利己或推己及人都是通過這種結構展開的。到底是“向外”還是“向內”,取決于一本與一體的倫理是否昌明,古人所謂的“明倫”即是此意。這也正如一個在團體格局中的人是自私自利還是大公無私也不取決于團體格局本身一樣,而是要看“神本”或“個體本位”的倫理在此格局中的普及程度如何。“神本”或“個體本位”的倫理在團體格局的社會中使人具有平等觀念和公共精神,在差序格局的社會中卻可能使人虛偽和自私;同樣,一本與一體的倫理如果放到團體格局的社會中,也未必能夠使人推己及人。在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中過度提倡個體化只能釋放人的私欲,未必能夠帶來真正的社會平等。
費孝通在描述差序格局時有一個著名的比喻,像石子投入水中的“水波紋”一般,本文的分析可以豐富這個生動的意象并賦予其生命意義上的動力。在差序格局的核心層,“一本”的垂直結構使得人人向父母和祖先致敬,然后依據與父母、祖先的聯系向外推及,如同一泓泉水,充積豐盈后方才潤澤萬物。《中庸》有云:“溥博淵泉”,此泉之本靜深如淵,唯其靜深如淵,出之為大江大河,才能溥博如天。當前的社會結構正經歷急劇的變化,個體本位的倫理與差序格局的結構沖突也正在加劇,這是我們理解許多現實矛盾和社會沖突的深層因素。若有一天中國人不再把家視為生命的源頭和歸宿,不再將生命的意義寄托于父母和子女的命運,不再有基于一本和一體的感通和感動,猶如枝葉離開樹干而花果飄零,中國社會的大變局才會真的完成。
注釋和參考文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