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都和文化》:覽歷朝古都悠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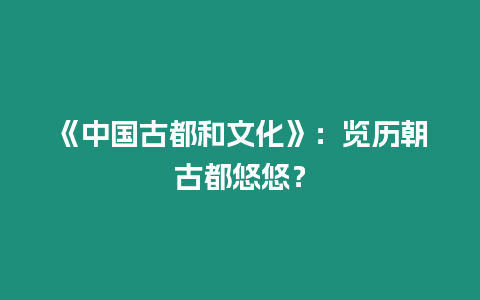
古都研究,是近代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中國古都學”。史學名家史念海先生,將此學科定義為“研究中國古都的形成、發展、蕭條或至于消失,或經過改革成為新的城市的科學。”在此領域中,大家輩出,著述繁巨。不止二三子可稱巨擘,而筆者認為,史念海先生仍可稱翹楚。
先生及弟子門人,名聲赫然者眾,在地理歷史研究領域,卓識洞見,聲聞海內。先生所倡之古都學研究,亦已漸成顯學,于今城市經濟文化發展諸方面,起著重要的輔助作用。
史念海先生說:“在我國的悠久歷史時期,曾經有過許多王朝或政權興起和滅亡。每一個王朝或政權都各有其都城,有的還不止一處。這些都城的存廢都可反映出各自的王朝或政權的若干面貌,諸如政治的隆窳、經濟的榮枯、社會的變化,以至國運的盛衰。這是因為都城為一代的中樞所在,五方雜處,從這里可以了解到全國的情況。了解和研究都城,有助于我們對歷史的研究。”
誠如其言,其暢行二十余年之大作《中國古都和文化》一書,堪稱此領域的入門秘籍,此次由重慶出版集團再次出版,或為學界幸事。
史先生的貢獻之一,是不但鉤沉了歷代古都之創建緣由和毀滅肇因,還將上古至民國諸種政權所據之地,都一一做了羅列。比如,陳勝所建張楚之都,位于今河南淮陽,雖6月而亡,卻史冊赫然。楚懷王之孫熊心所建楚都盱臺,位于今天的江蘇盱眙縣東北,政權僅存3月,但既然曾有都名,也在史念海先生的著作中,留下了一筆。
在史念海先生的著作中,各類性質的都,全部囊括在內,幾乎毫無遺漏,農民起義建立的臨時政權所設之都,亦一視同仁。難能可貴的是,周邊各族所建的都城,也都一一在冊。都名、建都時間,都較為詳盡地做了陳述。
自周始,都城根據統治的需要,就形成了雙都制,副貳者為陪都。史念海先生也專列一節,詳為鋪陳。
不唯如此,史念海先生對多如牛毛的大小都城,都做了年代考辨,比如,西安為都,經千余年;北京至民國上溯,為都時間也將近千年。
史念海先生的這部著作,有繁有簡、繁簡得當,其簡述條理清晰,其繁說則面面俱到,對古都進行了較多面向的研究。
比如,對于唐代里坊制,就落墨較多、專成一章。其中《唐代長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變遷》一節,對唐長安外郭的狀況,進行了全景式掃描。“里坊中雜有官署、寺觀、邸第、園囿,編戶亦錯居其中。”史念海先生不僅根據文獻提出觀念,如“為了易于維護,每坊四周都有圍墻,這和京城周圍有郭城一樣。這樣的圍墻,通稱坊墻。《唐會要》卷八六《街巷》,載有貞元四年二月的敕文,就曾提到京城內莊宅使界諸街的坊墻。也有稱為里垣的,白行簡所撰的《李娃傳》,就曾道及安邑坊東門之北的里垣。”為了證實其觀點,還引用了唐城發掘隊的當代考古研究,“證明了里坊確實是有坊墻的。”史先生做學問扎實,當然清楚在古代社會任何規定都有僭越者,因此,也援引相關資料,證明確有不法人家自開坊門,“當時雖然規定非三品以上及坊內三絕人家不許隨便自開坊門,可是未能遵守這樣成規的人還是不少,因而引起有關司事者的注意,甚至驚動了王室”。自開坊門,意味著里坊制的管制鐵板,被私自打開了缺口。正是對自由的渴望,對約束的沖擊,才有了若干這樣的知法犯法者。這樣的嘗試,也激勵了宋代沖破居住空間的管制束縛,營造相對自由的坊市格局。
史念海先生指出:“這些都城在演變的過程中是有一定的規律的。中國古都學不僅研究這些古都演變的過程和現象,而且研究其中演變的規律,研究出這些規律以為當前建設的參考。尤其是在古都的舊址上現代城市的改建和擴建,其間還有一層因襲和革新的關系。”
前人開山,后人修路。中國古都學雖然已經取得矚目成就,但為后來者留下的研究空間,仍然巨大。
在早期的帝國空間構建中,城市是體現著生產力發展和文明發展的顯性標志,就早期中國的情況來看,“都”是與宗教意識緊密相關的宇宙想象,隨著宗教觀以及政治權力與統治模式的演化,其內涵與外延也都發生著改變。
比如,春秋時,“都”還只是一個非常狹義的城市名詞,君所居之地曰國,大夫所居之地曰都。在宗教及文化層面,“都”的內涵還包括大夫及貴族所居所葬之地。據春秋時的墓葬研究,大夫們死后是葬在城內的,很可能離生前的居所不遠。離開了這一宗教觀的其他形式的“城”,可能都不能稱之為“都”。
到了戰國,“都”的內涵及外延繼續衍化,從祖宗所居之所,到宗廟所在之地,直到戰國晚期的秦,才成了天子所居之城。《左傳》給“都”的定義是:都者,有宗廟先君之主之謂都。
以秦為例,不斷遷都,至雍城,其建筑形態,也隨著秦的不斷發展壯大,呈現出從“重宗廟之儀”到“重天子之威”的轉折,從城市空間的布局上,已經展現出從宗廟中心制向宮殿中心制的過渡。到了嬴政建都咸陽時,為突出天子之威,皇宮成了國都中心,而宗廟已經降至次要地位,置于南郊。
漢代以后,人們不得不給“都”以新的命名: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直到漢惠帝的時候,才在長安城為漢高祖修建了一座祖廟,修建了市場和藏冰室,然后又修了內墻,把宮殿、太廟和市場都環護起來。
因此,從詞源學的角度,把“都”的概念向前回溯,我們還是存有疑問:西周與商,天子所居之地,是否可稱之為“都”。而到了漢魏以及遼金,“都”的政治、軍事、文化功能與戰國時又有不同。以遼之五京為例,除上京是政治中心外,其余四京只是方便控扼一方,徒有京名、而無都實。
那么,所謂的古都學的研究對象,到底是天子所居之所,還是拱衛京師、分權而治之城,都需要進一步明確概念,深入深究。“都”雖然被廣泛使用,但有時此都非彼都,有些“都”只是城的不同叫法而已。
在《中國古都和文化》一書中,史念海先生說,“都城之中,人事繁雜,林林總總,未能盡歸一律。”其言甚善。古都研究,也正如先生所言,期待后繼者披沙瀝金、詳加考證、分門別類、以便時人。
關于史念海先生在此領域之貢獻,王社教先生所評,與筆者心有戚戚,先生“發起和創立了中國古都學會,形成了一支穩定的學術隊伍;創建了中國古都學,奠定了中國古都學研究的理論基礎;堅持‘為世所用’的治學理念,指明了中國古都學研究的目的和方向;總結和勾畫出了中國古都發展的基本面貌和規律,推動了中國古都學研究的發展”。
冀望后來者以史念海先生為幟,借由古都研究而至文明研究,總結出一套“中國經驗”,則每一處斷壁殘垣所蘊藏的價值,都可堪夸耀、光輝永存。(作者:孫曉飛,系古都研究學者,著有《繁盛與衰敗:帝國三千年都城變遷史》等著作)
上一篇: 青春與夢想同行演講稿?
